1942年1月22日,香港戰火紛飛,病床上的蕭紅在砲聲中結束短暫的一生。
臨終前,她從枕頭下摸出紙筆,寫下兩行字:
「我要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
半生盡遭冷遇,身先死,心不甘,不甘。 」
另外半部已經寫成的紅樓,就是她的自傳長篇小說,也是最負盛名的代表作:
《呼蘭河傳》。
為這部作品作序的茅盾給予讚美:
它是一首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淒婉的歌謠。
也許很多人跟我一樣,一度以為這是長篇散文,是作者的人生回憶錄,因為人物那麼真實,文字又優美如詩。
真真假假,夢醒夢迷,誰能分辨?
每一部小說,都寫出悲歡離合的一生。
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部起伏不定的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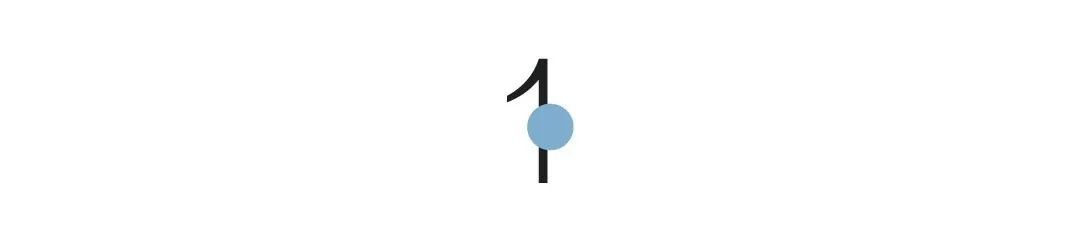
小城故事多
一個人走到生命盡頭,最懷戀是出發的地方。
蕭紅的故鄉,在東北偏遠小城呼蘭郡。
那裡有一條河,叫呼蘭河。
在《呼蘭河傳》中,她化作一隻鳥,在意念的時空裡飛回去,俯瞰曾經熟悉的春夏秋冬,芸芸眾生。
大地凍裂,西風似刀,老人鬍子上掛著冰溜。
賣豆腐的人的盤子,掉在地上就被拿不起來了。
賣饅頭的老頭被冰雪封住腳,走路像踏著雞蛋。
受凍的小狗哽哽叫著,腳爪像被火燒著一樣。
一起筆,蕭紅就將讀者帶進冰冷雪地,然後將那裡的街道商舖與人間煙火嘩道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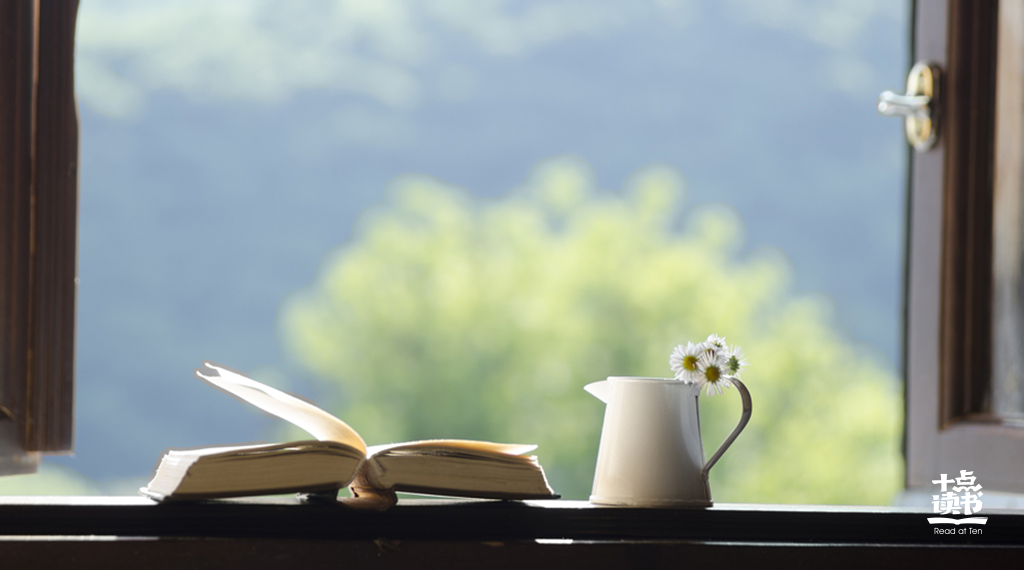
小城有兩條街道,分別是東二道街、西二道街。
西二道街晴天煙塵滾滾,雨天道路泥濘,乏善可陳。
東二道街有兩所學堂,一所在龍王廟,一所在祖師廟。
龍王廟裡的是農業學校,教孩子養蠶。
一到秋天,教員會把蠶炒了大吃幾餐。
祖師廟裡的是普通小學,上學的人形形色色,有私塾的教書匠、糧棧的管賬先生,還有當了孩子他爹的。
街上有個大泥坑,下了雨,變成河,就會出亂子——
人翻車,馬失蹄,淹死過小豬,泥漿悶死過貓狗雞鴨,放學的小孩掉進去,被路過的小販救上來…
這些,成為庸俗日常的點綴。
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柴米油鹽,各有各的哀樂和故事。
王寡婦賣豆芽菜維生,兒子淹死後,她從此瘋了,但照舊年復一年地賣豆芽菜,照舊靜靜地活著。
染缸房的學徒為女人發生爭執,一個把另一個按進缸裡淹死,活著的下了監獄。
豆腐坊裡,夥計打架,殃及池魚,把拉磨的驢子打斷了腿。
造紙房有個人,將私生子活活餓死。
街道外的胡同寂寞又冷清,大家關門過日子。
賣燒餅的人提著籃,一路吆喝,有人探出頭看看,有人問價,偶有媽媽領孩子出來買,孩兒們你爭我搶,最終打鬧起來。
賣麻花的走過,又來了賣涼粉的。
賣豆腐的收了市,火燒雲登場,千變萬化著。
她寫道: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來回循環地走,那是自古就這樣的了。
風霜雨雪,受得住的就過去了,受不住的,就尋求自然的結果。 」
小城裡的林林總總,都藏在蕭紅心底。
一回望,便能往日重現。
回不去的地方,叫做故鄉。
雖然回不去,心里安放著故鄉,也算一種幸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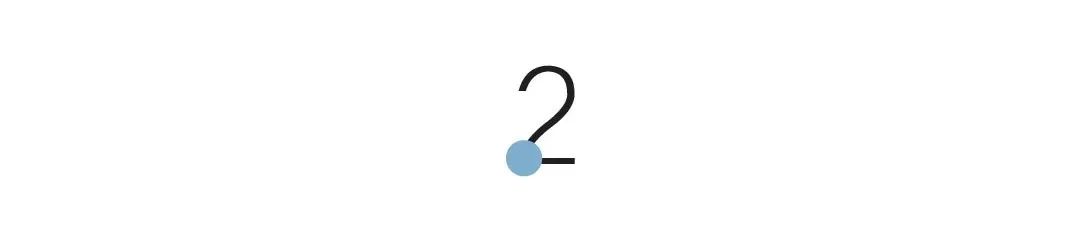
煙火之上的盛舉
一方山水,養育一方。
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每個作家筆下的故鄉,都具備不同的色彩和味道。
社戲、烏篷船、捏叉刺猹的勇猛少年。
“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
這是魯迅當年的故鄉。
小運河、石拱橋、東柵市民集散的財神灣。
「淡綠的河水慢慢流過,一圓片一圓片地拍著岸灘,微有聲音,不起水花。」
這是木心久違的故鄉。
蕭紅懷念中的故鄉,充滿那個時代北方鄉村的風土人情:
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燈、野桌子戲、娘娘廟大會…
不一而足。

大神穿奇怪的衣服,閉上眼睛,在那裡裝腔作勢。
百姓卻相信他能驅邪除魔,家裡有人生了病,總會恭敬地請大神。
跳的看,看的看,大鬧一場,病情也未有好轉。
回想觀看跳大神的夜晚,蕭紅不禁感慨:
「滿天星光,滿天月亮,人生如何,為何這麼悲涼。」
七月十五盂蘭會,男女老少都奔向河邊,呼朋引伴著去看河燈。
和尚念完經,吹奏起笙管簫笛,從上游下來的白菜燈、西瓜燈、蓮花燈成千上萬,照得河水幽幽發亮,水上跳躍著月亮。
大人看出了神,孩子拍手叫絕。
想起這一節,蕭紅興嘆:
「真是人生何世,會有這樣好的景況。」
秋天,靠天吃飯的人們透過唱野台子戲感謝神明。
搭戲台時,嫁出的女兒回娘家了,外地的親友也過來了。
眾人藉此機會團聚,閒聊近況,交換禮物,人情練達的文章寫在這種時刻。
除此之外,看戲也是洽談男婚女嫁的好時機。
有媒人牽線的,有父母敲定的,有酒酣耳熱之際指腹為親的,也有人不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私定終身,之後歷經諸多波折。
在蕭紅看來,那些波折,也許比《紅樓夢》更有趣味。
四月十八的娘娘廟大會,是為求子孫。
匆匆磕拜,然後走人,似乎並沒有尊敬之意。
走出廟門開始逛街,泥公雞、小笛、線蝴蝶、不倒翁…
琳瑯滿目的玩具惹得孩子一霎歡快一霎憂愁。
除了以上,還有其他風俗風物,讓她一時無法說清楚。
這些盛舉,在煙火之上,也在蕭紅心底盤亙,藉由她的手和筆,行雲流水於書卷。
深情的人,熱愛萬物。
否則,蕭紅不會將故鄉風物追憶得鉅細無遺,有時反諷,也帶著俏皮。

我家是荒涼的
為蕭紅寫傳的林賢治認為:
她是現代中國偉大的平民作家。
生在地主家庭,蕭紅從小接觸到租住自家房屋的底層民眾,他們艱苦的生活讓她難以忘卻。
養豬的,拉磨的,趕車的,開粉房的…
這些人貧窮又愚昧,在命運的泥淖裡苦苦掙扎。
因為閉塞和無知,他們身上發生悲慘的故事。
比如趕車的那戶人家。
「家風是乾淨俐落,為人謹慎,兄友弟恭,父慈子愛。」
也有例外時候——
娶了團圓媳婦,黑乎乎、笑呵呵、大方勤快的女孩,婆婆為了給她個下馬威,每天打一頓,打得連喊帶叫,不分晝夜。
打出了毛病,不惜重金請人跳大神,而且跳得出奇——
用大缸幫團圓媳婦洗澡,而且是當著眾人的面。
把團圓媳婦的衣服剝光,按進滾燙的沸水里,燙暈過去,冷水澆醒,如此再三。
沒多久,終於把活蹦亂跳的少女折磨至死。
即便死了,婆婆還要剪下她的大辮子,對外人說是自己掉下來的,以此證明媳婦是妖怪。
又例如在她家幫閒的有二伯,性情古怪,喜歡和貓狗鳥雀說話,和人在一起卻很沉默,即使開口,也都是很古怪的話。
有二伯很虛榮,別人喊他二東家、二掌櫃,他就笑逐顏開,誰喊他有二子、小有子,他簡直會氣紅了眼。
有二伯一生寄人籬下,無家無業,小小的一包行李,夜裡睡覺,鋪開,早上起來,捲好,彷彿每天都準備去旅行。
在童年的蕭紅眼裡,這是「耍猴不像耍猴,討飯不像討飯的」一個人。
有一次,有二伯又偷東西出去賣錢,被蕭紅的父親發現了,遭到一頓痛打。
打倒在地,他站起來,又被打到,他再站起來,又一次被打到。
最終,沒有力氣再站起,六十幾歲的有二伯就索性躺著,口鼻裡的血流淌在地,兩隻鴨子踅過來啄食那些血……
觸目驚心的場景,不動聲色地記錄。
見過各種兇殘偏僻的人生,蕭紅在書裡再三悲嘆:
“我家是荒涼的。”
對那些底層民眾的不幸遭遇,蕭紅懷著深切的悲憫。
然而他們的愚昧思想,又讓她感到悲哀。
如果不是家在這裡,再也不想回到閉塞的角落。
她曾這樣說過:
對繁華、開明、自由的嚮往,是她去往外面世界的根本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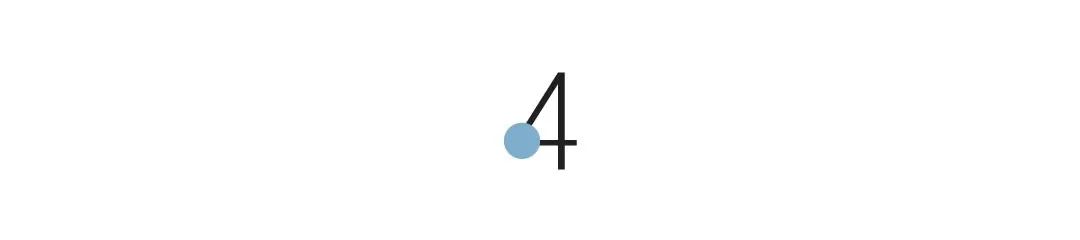
美麗大花園
漂泊十年,讓蕭紅念念念不忘的,是老家的大花園。
她用詩意而純真的文字描述那裡的種種:
花園裡邊明晃晃的,紅的紅,綠的綠,新鮮漂亮。
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
鳥飛了,像鳥上天了似的。
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
一切都活了。
都有無限的本領,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都是自由的…
父親為了貪婪而失去人性,母親也不怎麼愛她,精力都用在弟弟身上,祖母用針刺她手指。
蕭紅的童年很寂寞,卻也親近大自然。

她鑽進花園,與花草為伍,與蟲鳥作伴。
有時候,蕭紅鑽進蒿草叢,找一種叫天星星的野果子吃,吃睏了,就躺在草蔭裡睡覺。
最幸運的是,她有一個疼愛自己的祖父。
祖父性情散淡,不愛理財,家事都給妻子管理,他喜歡自由自在地閒著。
爺孫們常常整天待在花園,老的栽花,小的跟著栽花,老的拔草,小的跟著拔草,老的種菜,小的就在旁邊胡鬧。
孩童的心無邊無際,看見長大的黃瓜,跑過去,摘下就吃。
看見一隻大蜻蜓,丟下黃瓜又去追蜻蜓。
沒追幾步,又去採倭瓜、捉蚱蜢……
有時候,祖父蹲在那裡拔草,蕭紅摘來一大堆玫瑰花,用小草帽兜著,再一朵一朵插到祖父的草帽上。
他以為雨水大,所以花香很濃,她卻在一旁笑得直哆嗦。
當他後知後覺了真相,也大笑起來。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花園裡灑下祖孫倆太多笑語歡聲。
祖父是讀書人出身,常教蕭紅念詩。
那時候,她還小,不懂詩句表達的意思,只覺得大聲念誦的聲音很好聽。
蕭紅很喜歡《春曉》,念到「處處聞啼鳥」的「處處」這兩字,就高興起來,滿口大叫。
更喜歡“重重疊疊上樓台,幾度呼童掃不開”,只覺得越念越有趣味。
祖父摸著她的腦瓜說:
「快快長大吧,長大就好了。」
和祖父一起度過的那段時光,點點滴滴,從蕭紅的語調中,不難看出她的意猶未盡與深情懷念。
美麗的大花園,讓蕭紅的童年不至於盡是荒涼。
笑盈盈的祖父,讓蕭紅的生命有了溫暖底色。
她在一篇散文裡寫道:
「從祖父那裡,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惡而外,還有溫暖和愛。」
感受過愛,才知道怎樣叫做愛。
從此之後,蕭紅將這兩樣作為永遠的憧憬。
四海漂泊,一生追求溫暖與愛。

電影《黃金時代》中,蔣錫金有一段旁白,也是他對舊雨的悼念:
「幾十年的時光無情的流逝過去,當我們遠離了滿目瘡痍的戰亂的中國,人們忽然發現,蕭紅的《呼蘭河傳》像一朵不死的花朵,深藏在歷史深處。”
任時光流逝,生命消亡,藝術之花永不凋零。
多情的人,才能領略它的搖曳。
作者 | 江徐,80後女子,煮字療飢,借筆畫心。
圖 | 視覺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