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滅亡是有亡國之徵的,韓非子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篇《亡徵》的文章,介紹了種種可能導致亡國的特徵。其中有一種亡國之徵是這樣的:「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意思是處理國家大事喜歡挑選吉日良辰,敬奉鬼神,迷信卜筮,喜好祭神祀祖的,是國家將要滅亡的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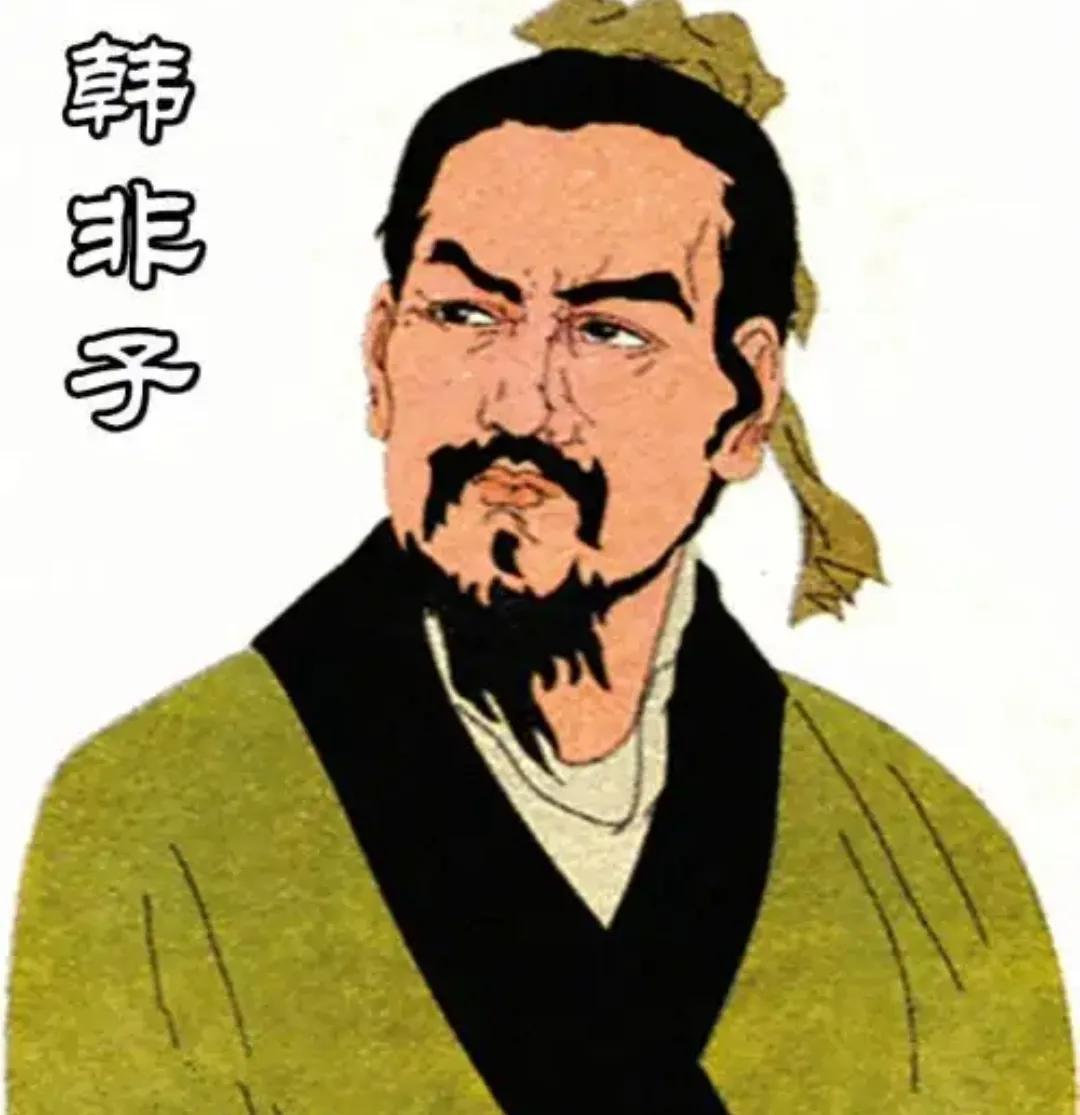
祭祀在封建時代是一種相當重要的活動,《左傳•成公•成公十三年》中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人認為一個國家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祀和軍事,否則國家會不穩定甚至滅亡。韓非子和《左傳》對於祭祀鬼神的態度表面上有一些矛盾,一個認為祭祀會導致亡國,一個認為祭祀可以保證國家穩定。
韓非子說的是迷信鬼神,一切大事都求助於祭祀。祭祀是封建統治者維護統治秩序的一種方式,在精神上控制廣大民眾。但統治者自己要是被祭祀給控制了,那就失去了祭祀的原本功能,給國家帶來危險。孔夫子認為對於鬼神要敬而遠之,要重視世俗事務的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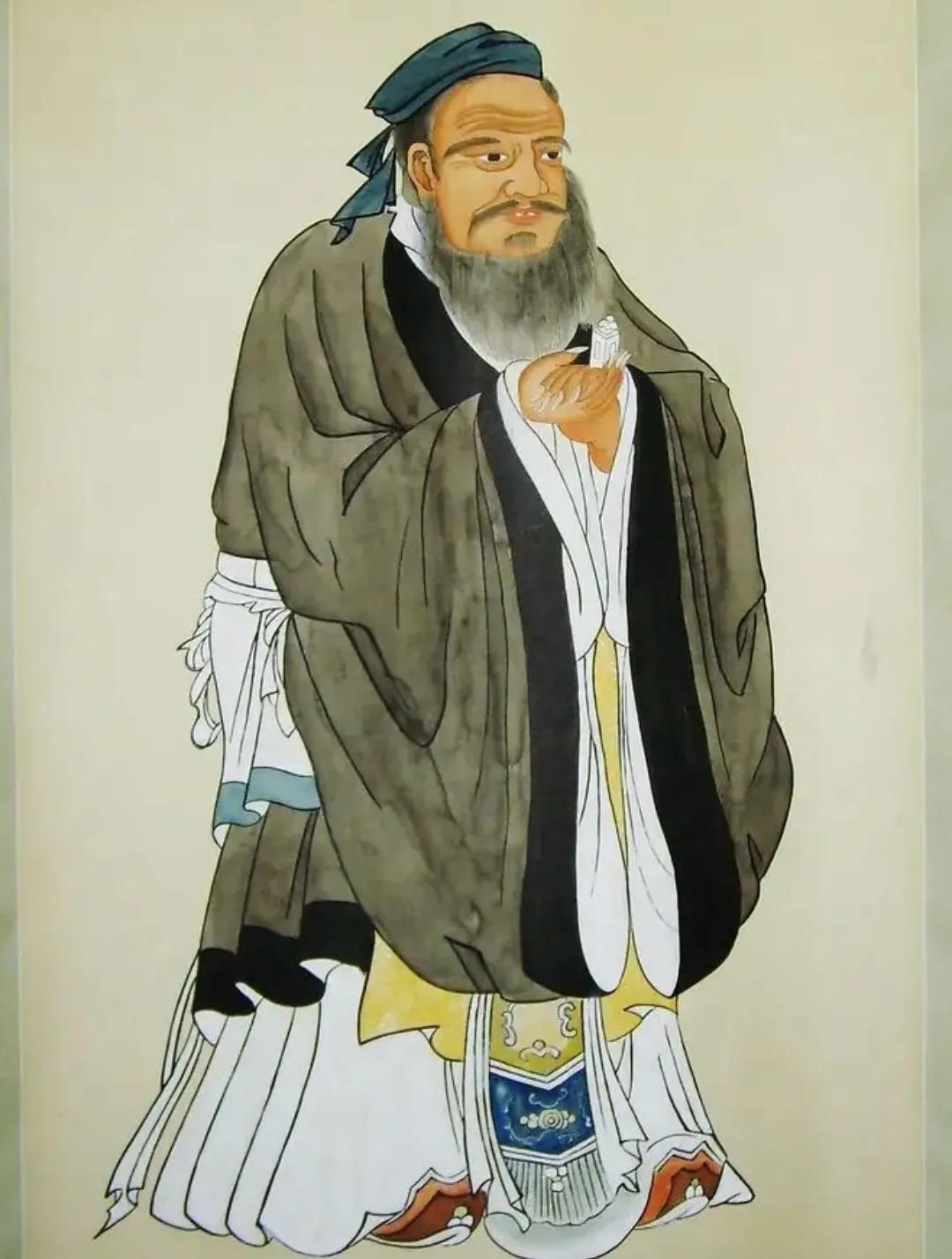
孔夫子不反對祭祀,但要控製程度。只要按規定的禮制去做就可以了,不能沉溺其中,不能過分。歷朝歷代對於祭祀都是有規定的,皇帝需要進行的祭祀,地方官員需要進行的祭祀,各級諸侯需要進行的祭祀都有明確的規定。不能僭越,也不能忽略,這是一套嚴密的製度。這套制度可以保證整個社會按照一定的秩序穩定運行。
至於祭祀的本質意義,早在春秋就已經被儒家先賢解釋了。祭祀天神是向天神展示自己代天治理子民的成果。例如獻上五穀,是為了說明天下五穀豐登,民眾都有充足的糧食,自己沒有辜負天神的信任。如果天下歉收,而獻祭大量的五穀,天神是不被接受的。所謂“民為神主”,重點在於民,而不在於神。

想讓神來賜福或者改變國運,那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君主自己的行為引起的,向神獻祭來求取力量保持國家延續是錯誤的。只有君主自己端正自己的行為,為民謀福,才能保證國家的穩定。一旦君主迷信祭祀,迷信占卜,不重視民眾福祉,那就是亡國的徵兆。
而宋徽宗就犯了這樣的錯誤。宋徽宗對神仙的迷信達到了不顧一切的地步,他自己親自擔任了神霄派的教主。為了自己的迷信,他舉全國之力整理道藏,完成了《萬壽道藏》的編撰;他在全國各地大建神霄宮,浪費了大量錢財,花石綱也與徽宗的迷信有關。

在徽宗的支持下,大宋興起了修道的熱潮,他自己也以「道君皇帝」為榮,所以許多人也都迷信道法。於是當金軍兵臨城下之時,大宋兵部尚書孫傅才會把希望放在了「六甲神兵」上,妄想靠神仙的力量反敗為勝,消滅城下的金軍。最後六甲神兵成了笑話,不但沒能擊退金軍的進攻,還間接導致金軍攻破了東京,讓大宋蒙上了靖康之恥。
對於迷信神仙的力量,妄圖依靠神仙的力量扭轉國運,早在春秋時代就已經有了教訓。當時的虢國面臨晉國的威脅,虢公不但不用心國政,還跑到莘之野侍奉神蹟。獻上祭品祈求神仙的護佑,當時的有識之士就認為虢國要亡國了。如此危急時刻,不去處理晉國的威脅,而求助於神仙,這就是昏聵的表現。果然虢國很快就被晉國滅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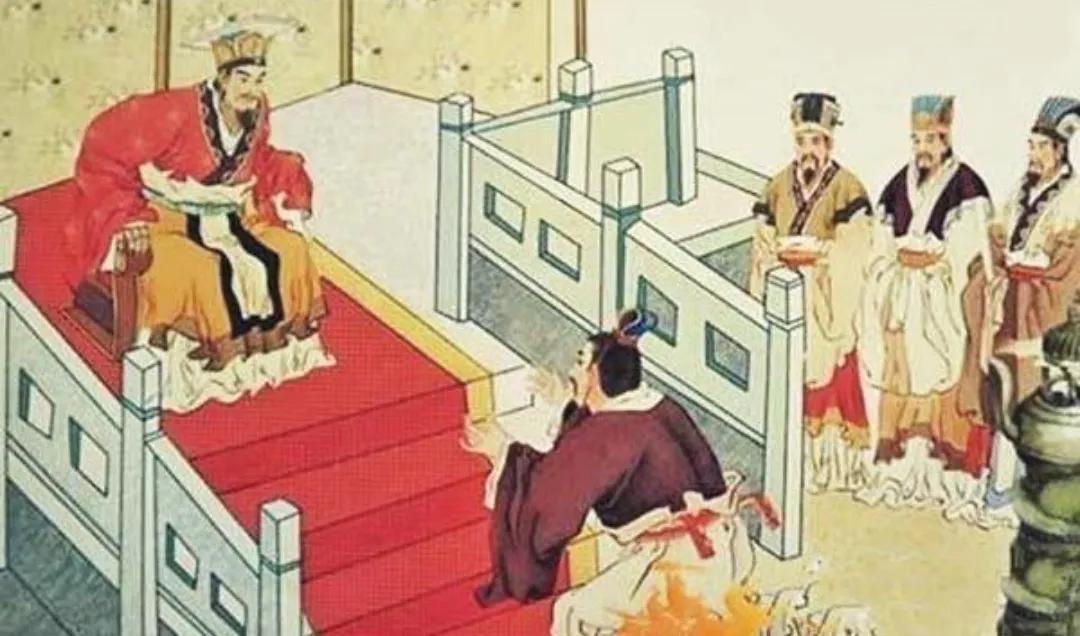
我國歷史上發生過許多這樣類似的事,迷信的統治者總是不斷出現。記得米果2020年大選時,白宮裡有一位女大師在開票時就一邊抽筋兒,一邊拍打桌子,並大聲祈禱“勝利!勝利!”,但最終懂王還是敗北,沒能勝過睡王。懂王應該是相信祈禱的力量的,但最終也沒有得到護佑。所以韓非子的總結很到位,“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