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24日清晨,當時北京的,中國第一大火車站-正陽門火車站,滿清官員人頭攢動,因為滿清五大臣今日啟程出訪歐洲,京城大小官員都到此歡送。
也是今日一名年輕的刺客懷揣炸彈,身著清隸僕役制服,喬裝隨從,從月台進入火車,以自己為人肉炸彈行刺五大臣。
最後一聲巨響,車站大亂,一片哀嚎,巨大的爆炸將火車頂炸開,滿清五大臣灰頭土臉、呆如木雞,行刺者壯烈犧牲。
這件事把慈禧嚇壞了,連夜命人將頤和園的宮牆加高了3尺,如今你去遊覽頤和園遺跡,還能看到當年留下的痕跡。
這是著名的民國刺客暗殺滿清五大臣事件,殺人者吳樾。
滿清末年,革命黨以暗殺反清,前僕後繼,視喋血捐生為人間快事。
1901年八國聯軍侵華後,把滿清按在地上摩擦,隨即西方列強坐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在華劃下勢力範圍,設置租界。
租界沿用西方管理方式,最大一個特點就是言論自由,這為革命黨人提供了避開滿清打擊和限制的樂土。
各種進步報紙、雜誌如雨後春筍在租界開設,揭露了滿清一直極力粉飾的滿清入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留發不留頭等。

這些言論讓滿清政府如芒在背,又沒辦法。 1903年由章士鑷主筆,章炳麟、蔡元培等撰稿的《蘇報》更是驚鴻一現,在上海英租界驚世騖俗,發表了鄒容的《革命軍》,首次公開號召推翻清政府,驅除韃靼,恢復中華。
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之間整個社會瀰漫著濃濃的反清氣息,加上清王朝鴉片戰爭以來對外作戰的穩定性發揮,只輸不贏,三天一賠款,五天一割地,讓包括許多「體制內的人」都心向革命。
《蘇報》的革命言論引起清政府極度畏懼,不顧租界規定派出衛隊突襲、查封報館,逮捕多人,鄒容在已逃出的情況下,看到其他人被捕後不願苟活,毅然選擇了自首,更是讓無數人為之嘆服和敬佩。
這讓整個租界的人,不管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站出來聲援被捕人員,加上本來清政府在租界就沒有執法權,這麼做也打了租界的臉,於是清軍被圍堵,來時容易,去時難。
最後此案留在租界依據西方法律審理,清廷只能作為原告,各方奔走相告,歡慶鼓舞,還未開庭滿清已經輸了。
審判結果是大部分人無罪釋放,僅2人獲罪也只是監禁,《蘇報》案產生的最大影響是讓反清的言論和行動從此走到明面上,不再遮遮掩掩。
暗殺時代
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全國各地的暗殺此起彼伏,讓清政府震驚的是這些刺殺沒有組織,完全是個人行為,這說明民憤之大。
1903年11月,革命黨人萬福華獨自策劃了在上海狙擊廣西巡撫王之春,拉開了晚清刺殺的序幕。
王之春藉法軍鎮壓過革命黨起義,而且親俄,是革命黨人的眼中釘,此次刺殺並未成功,萬福華用來行刺的槍撞針早已損壞,而他為了節省子彈,事前竟然沒有試用。事後,萬福華被判入獄十年,行動不成功,但打開了革命黨人的腦洞。
安徽桐城的書生吳樾深受觸動,認為這是對付賣國賊和推翻滿清統治的最好方法,當即寫下萬餘言長文《暗殺時代》,「夫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
而在1905年的中國,又發生了許多事:駐守旅順的俄軍向日軍投降;東京中國留學生舉行會議,敦促清政府實行立憲制度;寫下《革命軍》一書,因《蘇報》案被囚禁的鄒容病死監獄,年僅20歲;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
面對日益高漲的革命情緒,滿清政府為收攬人心,派遣載澤和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準備立憲。

但這5人全為戊戌變法事件後啟用的滿清重臣,換句話說都是不支持變法的,因為支持變法的都被清理了。
清廷此時的立憲實為一場拖延時間的騙局,只是為了緩和革命黨人的攻勢,面對全國請願要求加入開明人士的名單,清廷一概拒絕,坐實了「假文明之名,而行野蠻之實”,愚弄天下之心昭然可見。
革命黨人氣憤異常,慈禧身居深宮,難以接近,五大臣因此被推到風口浪尖,成為革命黨人的暗殺目標。巧合的是革命黨人楊氍麟曾留洋日本,此次被選為五大臣隨行翻譯。
因此,1905年初革命黨人即探得了考察的詳細計劃。剛開始革命黨人決定用手槍行刺,楊毓麟建議用炸彈,說:“手槍威力小,激發中途有時間停頓,五大臣身邊守衛森嚴,難以一舉殲滅。”
楊毓麟不僅出謀劃策,還積極張羅,透過熟人從英國購回威力驚人的炸藥,自製了炸彈,由於技術限制,最主要是無法購買到電動開關,所以炸彈的觸發設定為撞針式。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剩下的是誰去行刺?
手提三尺劍,割盡滿人頭
1905年夏,安徽蕪湖長街科學圖書社樓上,兩名健碩的年輕人在陳獨秀的見證下,決定以單挑的方式來決定刺殺滿清五大臣的任務歸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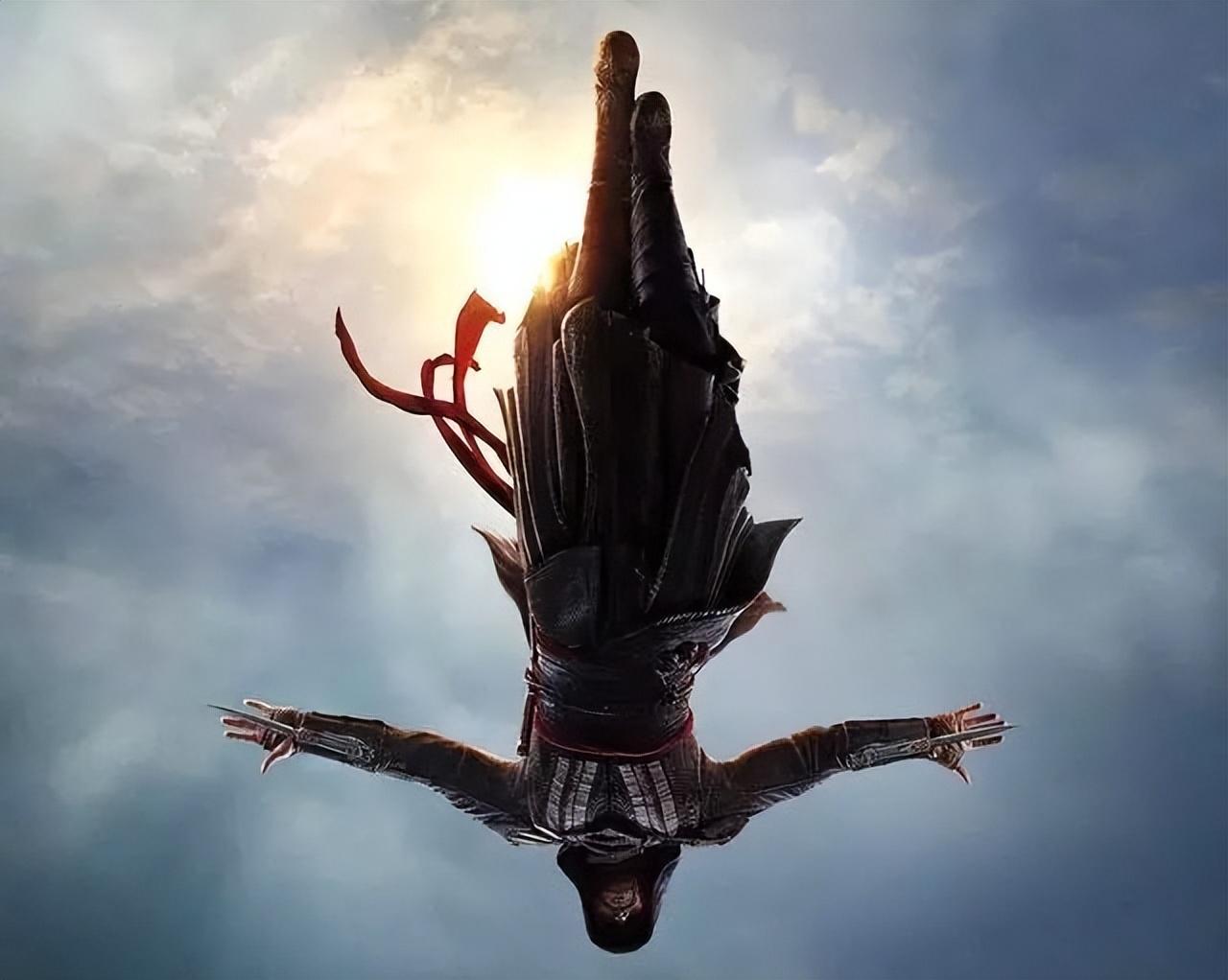
單挑的兩個人是28歲的吳樾和25歲的趙聲,作為裁判的是27歲的陳獨秀。兩個年輕人一番搏鬥後,難分勝負,精疲力竭,倒地喘息。吳樾突然問說:“死和推翻滿清哪個容易哪個難?”
趙聲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後者難。”吳樾笑道:“那就好,讓我來做容易的事,難做的就留給你了。”
最後吳樾拿下了此次暗殺任務,於是三人在樓頂取醉自茲別,臨岐贈寶刀,慷慨歌燕市,引頭成一快……
吳樾,晚清官宦家庭子弟,京師大學肆業生,是孫中山的崇拜者,更是一名刺客。吳樾本名吳越,古代官文舊例,犯人名字上要加偏旁,所以將"越"寫為"樾",後來大家統稱為吳樾。
他生於1878年,安徽桐城人,吳樾的父親在官府當差,小吏那類,職位低俸祿少,難以養家,乾脆棄官經商。
吳樾母親早逝,由兩位兄長撫養成人。吳樾從小酷愛詩詞,好遊俠,為人仗義,推崇李白《俠客行》「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吳樾的青年時代正好是滿清腐敗無能,被列強摩擦,頻頻割地賠款之際。吳樾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戊戌變法後放棄科考,跟隨父親打理生意,恥與滿清為伍。

在與父親走南闖北中,吳樾開拓了眼界和見識。 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高呼扶清滅洋,還刀槍不入,棄用一切洋貨之際,吳樾認為摒棄西方科技實為一種倒退,無力阻攔,那也不要為之添磚加瓦,於是去了運動影響較小的江南地區;
不久,戊戌變法失敗逃到日本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秦力山、唐才常趁義和團、清軍和八國聯軍火併,打得一團糟的時候,發起庚子勤王,組織自立軍,在安徽等多地舉事,計劃北上營救光緒皇帝,軟禁慈禧,然後繼續變法。
吳樾支持變法,聽到這個消息後倍受鼓舞,與幾位志同道合者收拾行囊,日夜兼程趕往安徽去入夥。然而才走到河北,秦力山、唐才常等人已經被清廷各個擊破,兵敗被殺,吳樾無奈打道回府。

八國聯軍侵華後,滿清在內外壓力之下,進行了一些改革,特別是在辦學上,由政府出資創建新型高等學堂,吃穿住行全免,除了傳統的儒家文化教學,還有外語、化學、物理等學科。
吳樾在通過保定高等學堂的入學考試後,順利入讀。此刻的清政府公辦學堂中,改變的味道四處彌散,新思想、新思維的報紙、書籍在學生之間公開傳遞。
吳樾受革命思潮的影響,由支持變法改為暴力推翻滿清,吳樾先是和趙聲、楊氍麟創建了北方暗殺團,伺機對清朝掌權者和大臣開展暗殺活動。
吳樾立誓“手提三尺劍,割盡滿人頭”,每日練習刺殺的專項技術——射擊、格鬥和引爆炸彈。
慈禧和奕劻,軍機大臣鐵良,袁世凱、張之洞等人都是吳樾的暗殺目標。不久吳樾的北方暗殺團迎來強強合併,被另一個革命大佬蔡元培吸收進光復會。在這裡,吳樾結識了大批革命志士,與陳天華、蔡元培、秋瑾、陳獨秀等私交甚厚。
車站悲歌
決定在火車站動手後,吳樾和另一個革命黨人秋瑾假扮主僕,多次前往火車站踩點,秋瑾原本要在這次行動中負責打掩護的,因另一個革命黨人徐錫麟準備在安慶發動起義,身為老鄉的秋瑾當仁不讓,回南方協助。
秋瑾臨行前,吳樾寫字相贈:“不成功便成仁,不達目的,誓不生還!”
吳樾寫給未婚妻嚴無畏的《與妻書》裡更是從容論述生死大義,嚴無畏也是一代奇女子,為吳樾賦詩《三絕》壯行。
行動前一晚,吳樾心無波瀾與朋友們暢飲至深夜,第二天早早起來,在懷中係好炸彈,同學張榕扮作僕人,直奔當時中國第一大火車站——正陽門火車站。
 中國鐵道博物館正陽門館
中國鐵道博物館正陽門館
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身為慈禧的紅人,月台上崗哨林立,站內為他們送行和溜須拍馬的官員把1500平方米的候車大廳擠爆了。
吳樾身穿一身朝廷侍衛裝束,閒庭信步走進大廳,跨上站台,他氣宇不凡,無人疑心,成功混入五大臣乘坐的專列車廂。
五大臣的車廂在第三節,越靠近這節車廂,戒備自然越森嚴。吳樾走到第四節車廂,這裡是五大臣的守衛和侍從專列,這些人坐在一起正在侃大山,看見吳樾進來其實並未疑心,畢竟是來自五個大臣府上的,誰認識誰啊。
不過多年當差習慣,例行的盤問還是不能少,一位侍從伸手攔住吳樾,隨便地問了一句:“兄弟,您是哪位大人的跟班?”
吳樾若無其事地應對:“澤爺!”稱呼鎮國公載澤為“澤爺”,乃是地道的京腔。
這不會有什麼破綻,但問題就出在吳樾的安徽口音上。吳樾一直苦練暗殺的硬實力,忽略了五大臣的隨從都是說北京話的。
吳樾濃濃的安徽腔引起了懷疑,狹窄的車廂通道內,幾個清兵狐疑地站起來,吳樾不慌不忙,鎮定地問道:“我是澤爺府上的,從安徽來京當差的。
吳樾掛著鎮國公的名頭,從其他地方調集親信也不是沒有過的先例,幾個清兵在沒搞清楚事情之前,也不敢用強,正在糾纏之時,火車突然啟動。
機車頭與車廂掛鉤鬆開的一瞬間,車身突然倒退,吳樾站立不穩,腳步一個趔趄撞在身後的清兵身上。
由於炸彈是自己研製,性能極不穩定,撞針被意外觸發,在吳樾的懷中爆炸了,吳樾下身被炸爛,當場身亡。

那個年代的炸藥還不是TNT,威力有限,第四節車廂被炸爛,緊鄰的第三節車廂爆炸中也就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五大臣中邵英傷得重些,但毫無性命之憂,除非破傷風,戴鴻慈與端方只受了點兒輕傷,其他人毫髮無傷。
張榕因為站得遠,未被爆炸波及,他迅速離開現場,回去後把吳樾的物品盡數毀去,化名餘本強藏匿起來。
但不久後,官兵就追查過來,將張榕抓獲,投入監獄,準備嚴刑拷打。張榕運氣好,一位獄吏聽聞後,被他們的義舉感動,恰好這名獄吏又屬於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於是把張榕放出來,兩人一起逃跑了。
這邊清廷震恐,慈禧嚇得膽戰心驚,不僅連夜加高頤和園宮牆,並派侍衛晝夜在宮牆下巡邏。
慈禧下令嚴查,卻無從知道吳樾是誰,為了驗明正身,清廷對吳樾的屍體進行藥物防腐處理後,陳列在車站玻璃匣中,懸賞辨認,但始終無人指認。
直到後來同盟會為頌揚和號召天下志士反清,把吳樾寫給未婚妻的遺書《與妻書》在日本東京刊登出來,世人才知道刺客叫吳樾。

在遺書中,吳樾希望未婚妻能夠參加革命「成為羅蘭夫人,他年與吾並立銅像」。羅蘭夫人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被雅各賓派送上斷頭台,臨刑前有名言:“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吳樾犧牲後,未婚妻嚴無畏悲痛欲絕,自知體弱多病,無法報仇,揮刀自刎殉情。孫中山贊其“浩氣長存”,吳樾所著的《暗殺時代》在革命者中爭相傳閱:“手提三尺劍,割盡滿人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