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 《孟子·滕文公下》說“墨翟之言盈天下”,《韓非子·顯學》也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其《外儲說左上》篇也有“墨子者,顯學也”的話)。但是秦漢以後,墨家似乎銷聲匿跡了,很少有人談及它。直到清代中期,才開始有學者整理校注墨子的著作。這個現象,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中是比較罕見的,其內因外因很複雜,這裡且不去討論,但有一個問題不能不提出來:兩千多年來墨子及墨家學派被冷落,導致人們對墨子思想的認識還不夠深入和準確。迄今的古代思想史、哲學史論著,大都認定“兼愛”“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這似乎已成定論。實際上,這樣解讀墨子很不准確,未得古人之心。那麼,究竟應該怎樣去理解墨子的思想核心呢?讓我們先從先秦兩漢學人的述評說起。墨子思想的基本內涵
墨子,名翟,魯國人,是墨家學派創始人。他的生平行跡,在《墨子》一書的《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等篇有些零散的記載。 《史記》沒有墨子的傳記,只在《孟子荀卿列傳》後面附有幾句話,說墨翟生活在孔子的時代,或是在孔子之後。根據清代以來學者的研究(如孫詒讓《墨子間詂·墨子年表》、梁啟超《墨子學案》等),墨子的生活年代,大致在孔子、孟子之間。他是手工業者,屬於城市平民階層,這個社會認同對他的思想影響甚大。
《漢書·藝文志》著錄《墨子》71篇,今存53篇。這部書的作者,一般認為是墨子的弟子,它包括了墨子本人及其後學的基本思想。
關於墨子思想的基本內涵,我們還是先來看先秦兩漢學人的述評:
《莊子·天下篇》評說墨子,指出他的思想主要有崇尚節儉(“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苛刻待己(“以裘褐為衣,以跂為服,以自苦為極”),主張兼愛(“汎愛”)、互利(“兼利”)、非攻(“非鬥”)、非樂(“毀古之禮樂”)、節葬(“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西漢初年成書的《淮南子》,在其《泛論訓》中介紹墨子思想說:“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其《要略》篇還指出了墨子節財、薄葬、簡服的主張。
再看《漢書藝文志》,它總結的墨家思想包括:貴儉、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尚同。
從以上簡述可知,先秦兩漢學人對墨子思想內涵的認知大致相同。他們指出的這些思想內涵,在今傳《墨子》書中都可以看到。
如果把先秦兩漢學人對墨子思想內涵的指認,與《墨子》一書結合起來看,那麼墨子思想的主要內容就更加清晰、確定了。 《墨子魯問》記載了這樣一段話:
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則)語之兼愛、非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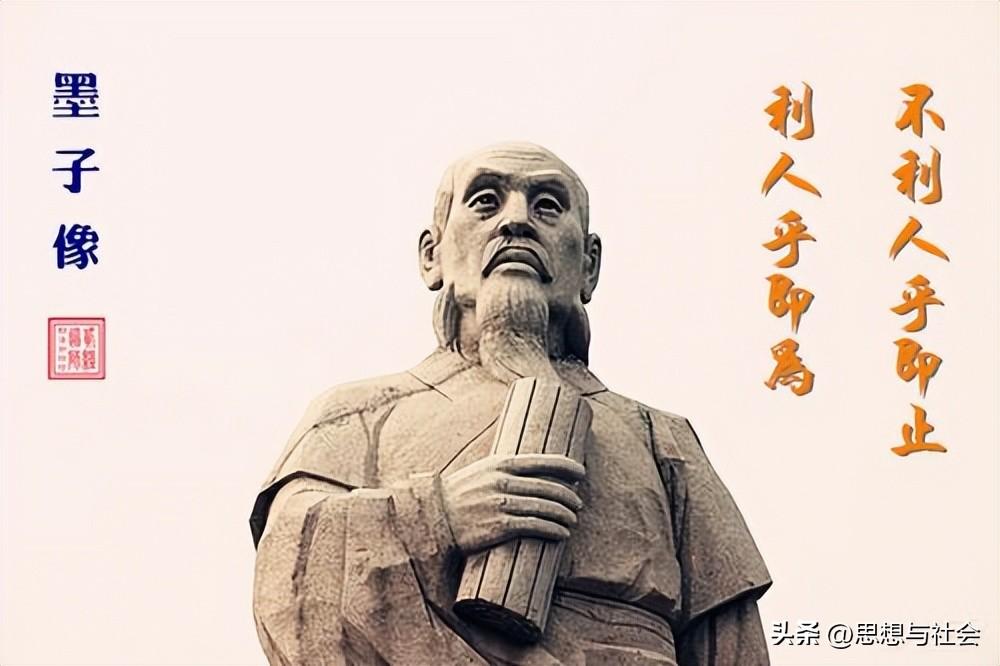
這是墨子自述的十條思想綱領,自然是墨子思想內容的可靠表述。顯而易見,先秦兩漢學人所述的墨家思想內容,與墨子自己所說,基本上是一致的。
根據墨子的述說語態或句式,墨子思想的這十條綱領,各有一定的獨立性質,它們分別針對不同的社會政治狀況而發。但是,十條綱領有沒有一個共同的精神,或者說十條綱領背後有沒有一個思想統領呢?當然是有的,這一點學者們都不否認。只不過,這個“精神”或“統領”是什麼,那就見仁見智了。較普遍的看法,是“兼愛”、“非攻”;我則以為是互利,用墨子的話說就是“交相利”,墨子思想的十條綱領,都是在這個核心觀念下展開的。
既然「兼愛」、「非攻」被廣泛認定為墨子思想的核心,那我們不妨就從這裡說起。 「兼愛」的實質與目的
墨子倡導的“兼愛”,就是“汎愛”、“博愛”,是普遍的愛、無差別的愛。 《墨子·小取》篇說得很清楚:“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週不愛人;不周愛,因為不愛人矣。”所謂“周愛人”,就是平等地去愛一切人,如果你不是愛所有的人,那就不叫“兼愛”了。
這個今天看來很好的思想,卻遭到孟子的痛斥:“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儒家也講“仁者愛人”(《論語·顏淵》《孟子·離婁下》),那為什麼孟子還要罵主張“兼愛”的墨子為“禽獸”呢?這是因為儒家“愛人”有一個原則,即要講等差倫序。 《論語·學而》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孟子·梁惠王上》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雲:'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孔子主張“泛愛眾”,孟子主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愛人”要恪守親疏近遠的倫理次序。首先要愛自己的父母兄弟,然後才能按照親疏關係逐次推及他人,這個倫理順序是不可侵犯、不能搞亂的。正因為墨子的“兼愛”主張平等地愛所有人,沒有區分親疏近遠,違背了倫理次序,孟子才說他“無父無君”,類同“禽獸”。與儒家“愛人”思想作一比較,墨子“兼愛”的內涵就更明晰了。
了解了「兼愛」的含義,接下來就要考慮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兼愛」是不是墨子思想的終極目的?如果不是,那麼他的思想核心又指向哪裡呢?
《墨子·兼愛上》中寫道:聖人治理天下,先要懂得社會亂像是怎麼產生的,才能進行有效的治理。那麼,亂像是怎麼產生的呢?是因為人們不相愛。子女愛自己卻不愛父親,這是“虧父而自利”;弟弟愛自己卻不愛哥哥,這是“虧兄而自利”;臣下愛自己卻不愛君主,這是“虧君而自利”——這就是所謂“亂”。反之亦然,父親愛自己卻不愛子女,這是“虧子而自利”;哥哥愛自己卻不愛弟弟,這是“虧弟而自利”;君主愛自己卻不愛臣下,這是“虧臣而自利”——這也是“亂”。推而廣之,盜賊愛自己的家卻不愛別人的家,所以盜竊別人家的財物以利自己家;搶劫者愛自己卻不愛別人,所以傷害別人以利自身;大夫愛自己的封地卻不愛別人的封地,所以攪亂人家的封地以利自家;諸侯愛自己的國家卻不愛別人的國家,所以進攻別國以利本國。這些就是天下的亂象。那麼產生這些混亂的原因是什麼呢?是不相愛。
在這裡,墨子指出不同人際關係之間的亂象,都是因為人與人不相愛,因此他主張“兼愛”,用愛來治理這些亂象。如果天下所有的人都能秉持“兼愛”之心,愛他人猶如愛自己,就不會再有混亂了。對待父、兄、君主就像對待自己,還會有不孝不忠嗎?對待子女、弟弟、臣下就像對待自己,還會不加慈愛嗎?把別人家看做自己家一樣,還會到別人家行竊嗎?愛護他人的生命就像愛護自己,還會有殘害他人的事發生嗎?對待別人的封地猶如自家封地,誰還會去攪亂人家的封地呢?對待別人的國家猶如自己的國家,誰還會去攻打他國呢?所以天下兼相愛就會大治,交相惡則必混亂。
不難看出,在墨子的論說中,“兼愛”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聖人治天下”,“兼愛”只是墨子為“治天下”開出的“藥方”而已。為達成某種目的而提出的方法或途徑,一般是不能當做思想核心的。
第二個問題,墨子提倡“兼愛”,是不是勸導以類似宗教式的無私愛心來治理社會呢?如果不是,它的實質又是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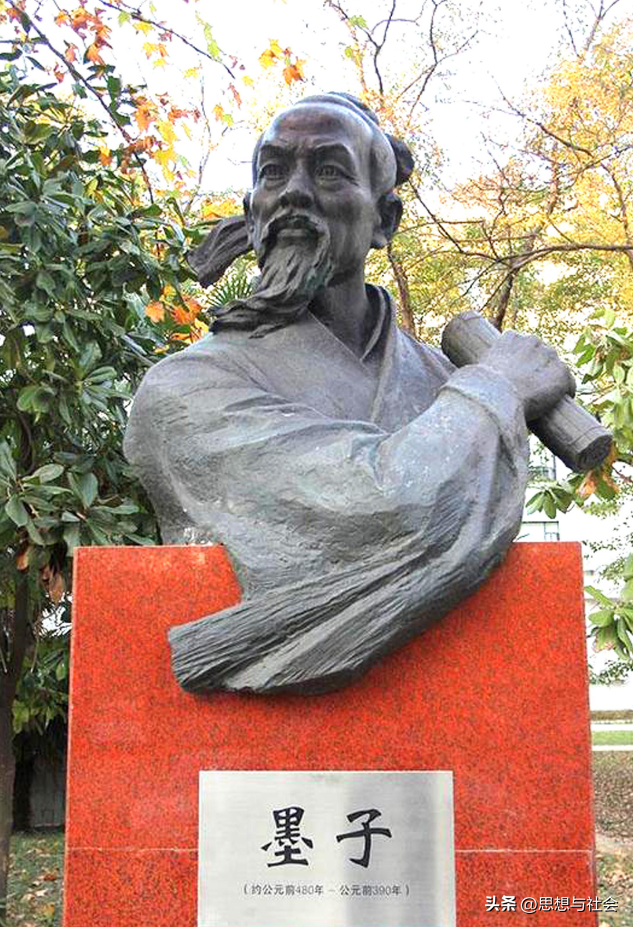
墨子論述以“兼愛”的辦法“治天下”,首先回答了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什麼叫做“治天下”,或者說“治天下”應該干些什麼事,達到什麼目的。這在先秦諸子,看法是不同的。比如儒家的孔孟講,治天下的準則和目的,就是要實現“仁政”“王道”;道家的老子講,治天下的準則和目的,就是要實現“自然”“無為”的政治格局;法家諸子則主張實現法制。墨子怎麼看呢?他說:“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兼愛中》)興利除害,這就是墨家治理天下的基本準則和目的。
理解了這個基本思想,我們再看墨子的“兼愛”之說,其理路就很清晰了:他反複分析指出,社會秩序混亂,是因為人們之間“不相愛”;既如此,就當然要推行“兼愛”;而“兼愛”本身並不是治天下的最終目的,興利除害才是目的,用墨子自己的話表述,這就是“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兼愛中》)。很明顯,墨子考慮問題的基點是“利害”,而“兼愛”不過是他興利除害的方法而已。因此,“兼愛”思想的實質是趨利避害,它並不是一種社會倫理的或者宗教意義的思想,而是為社會利益服務的方式。這個思想,與墨子手工業者的身份十分吻合,代表著城市平民階層的根本利益。
第三個問題,「兼愛」如何實現呢?墨子說實現「兼愛」並不難,他提出了兩個理由:其一,趨利避害是人們的共同心理,這是「兼愛」得以實現的根本基礎。現實的人生經驗是:「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兼愛中》)既如此,人們只要體認到「兼愛」就能「互利」這個好處,從自身利益的考量出發,就不難做到「兼愛」。其二,同時,也需要自上而下的規約引導,這是「兼愛」得以實現的製度保障。墨子說,只要在上位者勸說引導,並且輔之以賞譽和刑罰,讓人們真切體會到“兼相愛”則會“交相利”,“兼愛”就容易實現。
弄清楚上述三個問題,我們就能準確理解墨子的“兼愛”思想了,它的完整表達應該是“兼相愛,交相利”,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 「非攻」的實質與目的
墨子另一個著名主張是“非攻”,也被普遍視為他的核心思想。實際上,「非攻」也是實現「交相利」的手段而已。
《墨子·非攻上》篇寫道:如果有人跑到別人的園圃中偷竊桃子李子,大家知道了就會譴責他,執政者知道了就會懲罰他。為什麼呢?因為他做了損人利己的事。偷盜人家的豬狗雞這些小家畜,發展到偷馬牛這些大牲畜,直到殺害無辜的人搶劫人家的財物,他的不義行徑就越來越嚴重。為什麼呢?因為他給人造成的損失越來越多,讓人家損失越多,他的不義就越嚴重,罪過也越大。遇到以上這些情形,天下的君子都懂得譴責他,視為不義的行徑。可是,對於攻打別人的國家這種最大的不義行為,大家卻都不加譴責,反而讚譽為義舉。這能算是懂得義和不義的差別嗎?
以上這段話,墨子是圍繞著一個「義」字做文章,指斥偷掠攻奪是不義的行為,因此他要「非攻」。 《墨子》書中「義」字出現293次,並專有《貴義》一篇,說「萬事莫貴於義」。可見,墨子是非常看重「義」的。那麼,墨子所說的「義」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他說:
仁,體愛(以愛為體)也。 ……義,利也。 ……忠,以為利而強君也。 ……孝,利親也。 (《墨子經上》)
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謂愛利心在己);所愛、所利,彼也(謂愛利加惠於人)。 (《墨子經說下》)
顯而易見,墨子認為「義」就是「利」。這與孔孟把義和利對立起來並崇義黜利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把“義”和“利”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思想,墨子之前就有了。如《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記載趙衰的話:“《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 《左傳·昭公十年》晏子也說:“義,利之本也。”儘管他們尚未像墨子那樣把義和利直接等同起來,但也已經指出了二者的皮毛主輔關係。到墨子,不僅把“義”、“利”各自解釋,他還論證了“義”等於“利”的終極根據。 《墨子·法儀》說:“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法儀》篇主張“法天”而治,乍聽上去,似乎跟道家的主張相似,其實,墨子的“法天”與道家的“法自然”含義完全不同。道家的“法自然”是倡導“自然無為”,而墨子要效法天的什麼東西呢? “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這是天的意志;“兼而愛之、兼而利之”,這是天的行為。天的意志和行為方式,就是人類社會應該效法的準則。換言之,相愛以互利,就是最大、最根本的“義”,這是法天而行的,所以是“利”等於“義”的思想的終極依據,不容置疑。
明白了墨子之“義”的內涵,我們再回到“非攻”的論題。 《非攻》篇圍繞“義”字做文章,究其實質,是圍繞“利”字做文章。墨子考慮的是,攻伐之事在利益得失的衡量上不划算。他認為喜歡對別國發動攻伐的人,往往是以獲利為目的,但是就算你打贏了,“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意思是說,戰爭勝利的成果(如得到一些土地),對你而言沒有太大的用處,而且你所獲得的利益,還不如喪失的多。他舉例說:假如要攻奪一座方圓三里、加上城郭也就方圓七里的城池,戰死的將士必然多則上萬、少則上千,才可能攻占它。但是,對一個有能力攻掠的諸侯國來說,它缺少的不是土地,而是戰士和民眾。現在你要付出許多人的生命,去換取一座小小的廢墟城池,豈不是捨棄了不足的東西而爭取有餘的東西嗎?所以,攻城掠地並不是治國的要務。在墨子看來,當時各諸侯國的國情,是“人不足而地有餘”。顯然,墨子在這裡判斷義與不義,是以利害關係來衡量的。
既然攻伐不是明君善政,那怎麼做才是令人讚譽的善政呢?墨子又先提出一個判斷的準則:什麼是天下人所讚譽的善政?是“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符合天地、先祖和人民利益的政令措施,就是善政。據此來衡量攻伐戰爭,如上所說,是不符合這些利益的,反而是「天下之巨害」。所以,墨子要「非攻」。而「非攻」的目的,就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尚(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非攻下》)。顯然,墨子主張「非攻」的根本考慮和出發點,乃是一個「利」字,也就是《墨子·公孟》篇所說的:「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以「交相利」為核心的思想體系
墨子思想的十條綱領,除兼愛、非攻外,還有節用、節葬、非樂、尚同、尚賢、非命、尊天、事鬼。這八項主張,也都是以「利」為其思想基礎的。依照其思想內涵,我們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面向,簡單整理一下它們的邏輯關係。
一、節儉的民生主張
墨子提倡“節用”、“節葬”,並且“非樂”,用意都在務為節儉——節省物力民財。
《墨子·節用上》說:如果是聖明的君主治理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財富可以翻倍增長;如果是聖明的天子治理天下,天下的財富也可以翻倍增長。所謂翻倍增長,不是通過對外掠奪土地實現的,而是“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只要把國家那些奢侈無用的開支節省下來,財富就足以翻倍了。所以墨子說:“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這是“節用”的實質和意義。
《節葬下》說:厚葬死人,要有棺又有槨,要隨葬大量的物品,導致貧賤的人幾乎傾家蕩產,諸侯幾乎掏光府庫財物,這極大地浪費了有限的社會財富。久喪要求親人為死者守喪三年,守喪期間,守喪的人如是王公則不得上朝議政,士大夫則不能開展行政組織生產,農夫則不能耕種,百工則不能工作,婦人則不能紡織,這又是對社會財富創造力的巨大浪費。墨子總結說:“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已)成者,挾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意思是,厚葬使大量的財物埋入地下,久喪又長時間禁止人們創造新的財物;厚葬是浪費已有的財物,久喪是遏制將要新生的財物。無論厚葬還是久喪,都是對社會財富的無謂浪費,因此墨子主張“節葬”。
顯然,墨子倡導節用、節葬,是從“利”的原則提出的。 “非樂”的思想也是如此。 《墨子·非樂上》說:仁者所從事的事業,是為天下興利除害,“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並且,仁者考慮的是全天下的民生問題,從不為自己的感官是否愜意、身體是否安適而去謀劃什麼。因此,墨子主張“非樂”,並不是認為鍾鼓琴瑟竽笙之聲不快樂,不是認為刻鏤文章之色不美麗,不是認為芻豢煎炙之味不香甜,也不是認為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不安適,只是由於這些奢靡的東西“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所以他才“非樂”,也就是反對奢侈享樂的生活。
二、尚同的社會政治思想
墨子思想十條綱領中的尚同、尚賢、尊天、事鬼,組成了他的社會政治思想。這個政治思想,是以“尚同”為核心的。那麼,“尚同”是什麼意思呢?
《墨子·尚同上》從社會政治管理的起源說起,他說,遠古初民社會還沒有首領的時候,如果要議決一件事情,每個人都會有一個主意,人們的思想行動沒辦法取得一致。為了避免因“天下之人異義”導致社會混亂,事功不成,大家公選出了天子,並選立了三公、諸侯國君、政長(就是各級官吏),這樣建立起一套管理體制。而這套管理體制的要義,是維護“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的專制,保障“上同而不下比(比即同)”,即保證向上認同、服從而不是相反。因此,所謂“尚同”就是“上同”,就是自下而上的認同和服從。之後,墨子用長篇大論,從裡到鄉,從鄉到國,直到天下,闡說各行政層級都必須“尚同”的意義。
在墨子“尚同”的思想中,還有兩點頗可注意:
第一,是尚賢。他在述說各層級官吏體制的建構中,不斷重複“選擇賢可者”這句話。什麼樣的人是墨子眼中的賢者呢?他說:“賢者之治國也,蚤(早)朝晏(晚)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充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暮)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墨子·尚賢中》)很明顯,墨子所謂“賢者”,都是能夠給國家、萬民帶來利益的人。與此相關,他為如何培養更多“賢者”所提出的方案,也是以“利”為激勵:“譬若欲眾(增多)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眾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尚賢上》)“富之貴之,敬之譽之”,就是用財富名位去獎賞“賢者”,以期造就更多的賢能之人。儒家也“尚賢”,但是其一,儒家之“賢”是仁義道德楷模,不是墨家所說的社會利益創造者;其二,儒家之“賢”追求“仁政王道”,而墨家之“賢”追求“官府實”、“萬民富”。兩家關於“賢者”的內涵及其追求目標都是不同的。
第二,是尊天、事鬼。上面說到,墨子講“上同”,從裡到鄉,從鄉到國,從國到天下,都必須逐級向上服從。那麼,到了天子這裡,已經是行政的最高層級,他就可以為所欲為,不必服從誰了?不是的。墨子說:「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災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災戾疫、飄風苦雨薦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簢盛,以祭祀天、鬼。所有的人(包括天子)都必須「上同」於天、鬼。
為什麼要“上同”於天呢?因為天明察秋毫,普惠萬民沒有偏私,賞罰必信:“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墨子舉例說:以往三代聖王禹、湯、文、武,就是敬順天意而得賞的;三代暴王桀、紂、幽、厲,就是違逆天意而得罰的。敬天就能得利,逆天就要受害,所以要“上同”於天。
何以要“上同”於鬼呢?首先要知道,墨子所說的“鬼”,“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也就是天神、地祗、人鬼,是天地人的神靈,不僅限於祖先。這些神靈,與天一樣,也具有“賞賢而罰暴”的神力:“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墨子》本有《明鬼》三篇,今僅存其下篇。這篇文字,以鬼制人的旨意非常鮮明,並且,由於文中大量講述上古聖王信鬼尊鬼而得賞、暴王不信鬼不尊鬼而得罰的故事,更體現了以鬼制天子的含義。而以鬼制人的目的,還是要“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三、非命思想的實質
墨子鮮明地反對命定論(宿命論)。持命定論者說:“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墨子則認為,無論家國天下的治亂還是個人的窮達榮辱,都不是命定的,而在於人怎樣去作為,“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墨子·非命下》)。
墨子進而批評命定論乃是害人之道,他說:如果大家都相信宿命,就會導致在上位者不治理國政,在下位者不做事增財。上不治理,刑法政治就要混亂;下不做事,社會財富就不生產。社會財富如果不足,那麼,對上沒有供品以祭祀上帝鬼神,對外沒有資財以接待外國賓客、吸納天下賢士,對內沒有物資以救助飢寒、贍養老弱。所以墨子說,命定論是害人之道。
可見,墨子批評命定論,他的思想基點仍是「利」。相信命定,則會「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只有像上古聖王那樣,“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會“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從而實現“天下萬民之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