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籍(約766年 — 約830年),字文昌,少時僑寓和州烏江(今安徽省和縣烏江鎮)。都說出名要趁早,但年近半百時還困在生活的一地雞毛中,不知前途所在,雖然沒有被貶諦的跌宕,但張籍的官仕之路異常艱辛。還好他一路上遇到了那麼多的好友,摯友,有他們的相伴扶持,終於走出泥濘。
韓愈:仕途上的伯樂
貞元初,二十歲左右的張籍離開安徽烏江老家,來到魏州(唐代魏州轄境相當於今河北河南山東三省交界處)求學。長期漂泊,求學求仕都收穫寥寥,只好回到老家邊學習邊待業。
貞元十二年(796年),孟郊遊覽至和州,聽說當地饒有聲名的詩人張籍,便來拜訪,兩人都是門第衰微落魄之人,對詩學人生做了細緻切磋,大有相見甚晚之意。
認識孟郊對張籍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孟郊是他後來遇到伯樂的引見人。
貞元十四年,張籍北遊,經孟郊介紹,在汴州認識韓愈。韓愈對張籍的才學品行非常欣賞,留張籍在他的城西館讀書。張籍的人生開始跟韓愈變得緊密起來,張籍是個虛心學習的“大學生“,韓愈是個有能耐的“小老師”,後人都說,張籍是韓愈大弟子,雖然張籍比韓愈還要大幾歲。
韓愈當時已進士及第,在宣武節度使董晉手下任觀察推官。期間汴州舉進士,韓愈擔任考官,張籍參加應試列第一,被舉薦到長安參加國考,及第,這時候張籍已經35歲了。同樣是進士及第:柳宗元21,劉禹錫22,韓愈25,白居易28,孟郊46歲,羅隱「十上不第」。貨比貨得扔,可見人不能比人。
有了學歷,張籍開始了到處找工作的生涯。
張籍最大的人脈關係就是韓癒了,韓愈是個耿直boy,比較愛折騰,一不小心被貶諭,從中央調到地方當縣令,過了一年多才被召回長安。這時距離張籍進士及第已經過了五年,到處遞履歷的張籍終於得到關照,元和元年(806年)調補到太常寺當太祝。
太常寺是主管皇家祭祀社稷、宗廟和朝會、喪葬等禮儀的一個部門,太常有丞(總管),商官有六太: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等十幾個屬官。
太祝具體做些什麼呢? 《唐六典》中說太祝三人,正九品上,凡國有大祭祀,盥洗奉匜,既盥洗奉巾悅。是說國家有大祭祀時,負責給太常端水淨手遞毛巾,太常將祝禱詞敬上祠所,太祝等人跟隨一起跪讀祝文,禮成而焚之,以傳達與鬼神所知。
太祝不是台柱,只是個品級低下,俸祿薄微,與天子幾乎不得見的底層小吏,期間張籍又患目疾,幾乎失明。當太祝福的十年是張籍人生中一段窮困,辛酸,悲涼的歲月。
張籍感嘆「老大登朝如夢裡,貧窮作活似村中。未能即便休官去,慚愧南山採藥翁。」曲折百般好不容易做上了官,日子卻還窮的像村中農夫一般,但終究在帝都有了落腳處,太祝這小吏之職雖卑微,但卻沒有勇氣辭去。
張籍家裡有多窮? 「空堂留燈燭,四壁青螢「,家裡除了四面的牆壁,只剩下一盞昏暗的燈燭了,跟貧困生孟郊的家庭情況半斤八兩,兩人堪稱寒門學子奮進拼搏自強不息的代表了。
不僅生活過得拮据窘迫,心靈上更是屢受打擊。 《早春閒遊》中說「年長身多病,獨宜作冷官。從來閒坐慣,漸覺出門難。」自己久病不能做事,終日閒坐宅在家裡養病,以至於對社交心生恐懼,快要不敢走出家門。
「身病多時又客居,滿城親舊盡相疏”,久病不愈,親友們也漸行漸遠,沒人殷勤來探望。親友疏離也不可怕,《晚秋閒居》說「家貧常畏客,身老轉憐兒「,可怕的是太過拮据,有朋友來了家裡都沒有什麼可拿來接待的。
年老蹉蹉自己混成這樣就這樣了,讓人心生可憐的是自己的孩兒們,他們跟著身陷困頓,缺衣少食,自己不能成為他們堅實的依靠,簡直不能太辛酸。
太祝這個職位不但沒能給予張籍房子車子這種物質上的安全感,慢慢的,張籍發現自己人生沒有目標,特別無趣,這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孟郊在《寄張籍》裡說「未見天子麵,不如雙盲人。賈生對文帝,終日猶悲辛。…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爾珍。天子咫尺不得見,不如閉眼且養真。 “張籍與天子離得很近但卻沒有機會得見,雖然沒有失明,處境卻似乎跟個瞎子一般,如同賈誼面對漢文帝”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的遭遇一般,張籍空有滿腹才學卻懷才不遇,壯志難酬。
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賤貧。病眼街西住,無人行到門。」白居易感嘆:讀你的樂府詩,既能看到你關心社會民情,針砭現實、指斥時弊的思想內容,也能看出平易通俗,直切明暢的藝術風格,如此優秀的詩才學問,為何年近五十卻官小身微,上不曾“治國平天下”,下不曾“官”耀門楣,仕途既不通,“錢”路又出奇的促狹,住在遠離市中心的偏遠郊區,陷在病痛與貧困之中,門可羅雀?
白居易覺得不應該啊,在《酬張太祝晚秋臥病見寄》裡說「高才淹禮寺,短羽翔禁林「感嘆其滿身才華,被禮寺消磨淹沒,感慨其時運不濟,可惜可悲。
夜空中總有最亮的星,在一地雞毛中掙扎的張籍有個最堅實的依靠,那就是跟他亦師亦友的韓愈。三毛說:朋友這種關係,最美在於錦上添花;最可貴,貴在雪中送炭。雪中送炭,貴在真送炭,而不是語言勸慰,炭不貴,給的人還真不多。
《酬韓庶子》中說 「家貧無易事,身病足閒時。寂寞誰相問,只應君自知「。我身陷睏頓疾病,百事不易之時,還好有韓愈噓寒問暖,關心探望。
《酬韓祭酒雨中見寄》「雨中愁不出,陰暗盡連宵。屋濕唯添漏,泥深未放朝。無芻憐馬瘦,少食信兒嬌。聞道韓夫子,還同此寂寥無幾。這些生活上的糟心痛苦都可以對韓愈傾訴,不必遮羞,不用躲閃,他總能給困難中的自己最大的支持和無限的理解。
在人生低谷,張籍深深感激韓愈給予他的鼓勵與陪伴。

白居易:心靈上的知己
如果說韓愈是張籍仕途上的伯樂,像家人般不離不棄的給予支持幫助,幫他走過最泥濘的路,那與白居易的結交就是在泥濘路上最珍貴的收穫。
進入太常寺當太祝的這段時間,他發現有一個年輕人,他寫的詩歌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這與自己的詩文初衷多麼貼合,他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不正是自己追求學習的創作理論嗎!
這位年輕人正是「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考場贏家白居易,但這段時期白居易初入官場,官並不大,先後任秘書省校書郎、周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安史之亂中杜甫就曾經做過此官。
張籍想去拜訪白居易,他寫下一首《寄白學士》「自掌天書見客稀,縱因休沐鎖雙扉。幾回扶病欲相訪,知向禁中歸未歸。」表達了自己想要結交拜訪的心情。白居易收到後立即回覆《答張籍,因以代書》「憐君馬瘦衣裘薄,許到江東訪鄙夫。今日正閒天又暖,可能扶病暫來無。」向張籍發出了熱情的邀請,鄙人不勝榮幸,今日天暖又得閒,我隨時恭候您的到來。
張籍拖著病體來了,白居易將兩人的好久不見,惺惺相惜的心情在詩中作了詳細的記錄。
酬張十八訪宿見贈 自此後詩為贊善大夫時所作
昔我為近臣,君常稀到門。
今我官職冷,君君來往頻。
我受狷介性,立為頑拙身。
平生雖寡合,合即無縹磷。
況君秉高義,富貴視如雲。
五侯三相家,眼冷不見君。
問其所與遊,獨言韓舍人。
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倫。
胡為謬相愛,歲晚逾勤?
落然頹簷下,一話夜達晨。
床單食味薄,亦不嫌我貧。
日高上馬去,相顧猶逡巡。
長安久無雨,日赤風昏昏。
憐君將病眼,為我犯埃塵。
遠從延康里,來訪曲江濱。
所重君子道,不獨愧相親。
這首詩寫於為母親守孝三年結束回到長安,皇帝任命他做左贊善大夫前的一段時間,所謂善贊,也就是向太子宣講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是陪伴太子讀書的學官,沒什麼油水和權勢,是所謂的「冷官」。
白居易覺得張籍很是與眾不同,昔日自己身為近臣不斷晉升時,他們沒什麼交集,如今閒官冷職,彼此反倒頻繁來往起來,而且五侯三相家,往往見不到張籍的身影,可見張籍不是熱衷權力富貴,曲意逢迎之人。
兩人彼此謙遜一番,我這個人性子孤僻,沒有沒有,我才是,我還頑拙愚笨,很少跟他人合群。兩人確認過眼神,你就是那個對的人。
張籍說自己不擅長交集,平常只跟韓愈來往最多,其次就是白居易你了。白居易表示韓愈好厲害的樣子,自己望塵莫及。但張籍表示我個人其實非常喜歡你們的詩歌風格,你們推行的新樂府詩歌,多麼有杜甫的風範……兩人以道義相交,趣味相投,互相欣賞。
英國詩人赫巴德說,一個不是我們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應該具有「無所求」的性質,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就轉化為某種外在的裝點。如果說韓愈與張籍之間有著某種依存,功利或者說契約,那麼他和白居易的友情則更為純粹獨立,既不從屬於謀生也不依附於事功,是兩個獨立的靈魂之間的呼應與確認,讓他們兩人即使分開也獨而不孤。
由此,新樂府詩歌作者群中加入了一個實力派寫手,白居易寫勞動人民悲苦生活《杜陵叟》,《賣炭翁》,張籍就作《野老歌》。白居易寫貧富懸殊階級對立《輕肥》《紅線毯》,張籍就作《猛虎行》。白居易同情婦女不幸遭遇《井底引銀瓶》,張籍作《妾薄命》……堪稱並肩作戰的戰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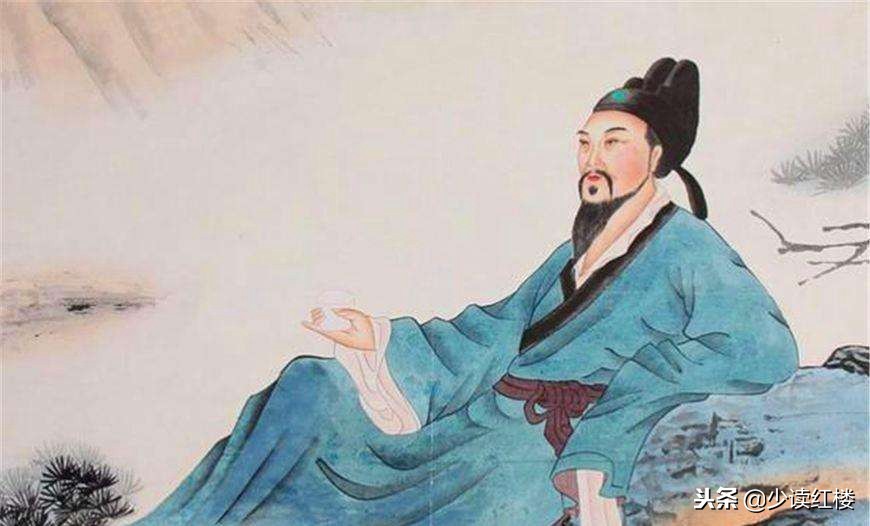
尾聲: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元和十年(815年),藩鎮割據愈發嚴峻,朝中發生刺客殺死宰相武元衡的大事,白居易本已不是左拾遺諦官身份,卻義憤填膺搶著上書要求緝拿兇手,被認為越職言事,後來又被誹謗,貶諦到江州任司馬。
元和十一年,張籍否極泰來,在韓癒的極力舉薦下轉國子監助教,去國家最高學府教書了,心裡不再那麼憋屈,眼病也漸漸好轉起來。
元和十二年韓愈隨宰相裴度出征淮西,平定藩鎮。同年淮西平定後,因功授職刑部侍郎,一時風光無限。元和十四年,割據多年的藩鎮被平定,一片祥和,憲宗皇帝派使者前往鳳翔迎佛骨,以此慶祝,祈求國運昌盛。但韓愈直率好折騰的本性又按耐不住,站出來給皇帝科普無神論,上《論佛骨表》極力勸諫,要求將佛骨燒毀,不能讓天下人被佛骨誤導。
皇帝覽奏後大怒,要用極刑處死韓愈,裴度、崔群等人極力勸諫求情下,貶為潮州刺史。 《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說的就是這件事。
元和十五年(820)夏,白居易被召回長安,任尚書司門員外郎。韓愈被貶後積極認錯,同年,被召回朝任國子祭酒(古代教育系統的最高職位),於冬季回到長安。長慶元年(821年),張籍受韓愈舉薦為國子博士,不久遷水部員外郎,又遷主客郎中。
一番風雨後,好像該迎接太陽出來照耀大地了。白居易度過了在江州被貶諦的歲月,韓愈從潮州回來,還被提拔升官了,張籍屢屢升職,眼睛恢復健康,好像該到歲月靜好的時刻了。
但一切都在慢慢變化,張籍有點後知後覺。
白居易跟以前有些不一樣了,他曾說過:“僕志在兼濟“,但貶官江州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一片赤誠換來的是難以排遣的痛苦,他說自己“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歸來的白居易不再那麼憤青,也不再樂於充當大眾公知,曾經引以為傲的新樂府運動不知何時拉起了帷幕,兼濟天下慢慢變為「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的獨善其身。
白居易不再熱衷於名利權勢,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被任命為杭州刺史,白居易走了,離開了人人都削尖腦袋也要往裡擠的帝都。
長慶元年(821年)七月,韓癒由國子祭酒轉任兵部侍郎,隔年,又轉任吏部侍郎。官越升越高的同時韓癒的身體越來越差,長慶四年(824年)八月,韓愈因病難以繼續工作告假養病回家,同年十二月,韓愈逝世。
天下無有不散筵席,就合上一千年,少不得有個分開日子。對韓愈白居易來說,張籍可能只是他們眾多朋友中較獨特的一個,但他們對張籍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如今韓愈故去,白居易遠離長安,剩下煢煢孑立的張籍。
回首人生已過多半,曾經或為養家糊口,或為爭名逐利,那時日子過得忙忙碌碌,如今不必再為紛擾雜事殫精竭慮,卻感覺心裡孤零零的,比以前更空虛。
人生的因緣際會確實如此,一路相逢,又一路告別。 《贈王建》「白君去後交遊少,東野亡來篋笥貧。賴有白頭王建在,眼前猶見詠詩人。」他們去的去走的走,偶爾跟年少時的朋友王建聚聚的時候還能聊一聊,聊一聊曾經的人事物。
張籍不擅長做官,但作詩卻能別出心裁,王安石評論張籍的詩說:「看似尋常最奇在意,成如容易卻艱辛。」他寫《秋思》 「洛陽城裡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
面對藩鎮高官的垂青,他用最委婉的詩句來回拒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委婉曲折卻又意志堅決。
張籍的朋友現在我們看都是大腕,唐朝聲名最大的師者韓愈,苦吟詩派代表賈島孟郊,詩魔白居易,宰相裴度,詩豪劉禹錫……張籍曾經因貧窮體會過人群中的孤獨,熱鬧是他們的,我什麼都沒有。但更幸運的是這些朋友帶給他的支持鼓舞,讓他變得從容,恬淡,溫和,堅定,讓他比別人更不怕一個人獨處,用一顆平常心,面對萬千事。
寶曆二年(826),一位從浙江赴京趕考的考生拜見張籍,從書囊中拿出自己的詩文呈給張籍,期望得到引薦,好順利取得功名。考試結束,等候揭曉的日子裡,仍覺忐忑不安,便寫了一首《閨意》「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君:「畫眉深淺入時無? 「把它呈給張籍,來試探考試結果。張籍看了,作《酬朱慶馀》「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足時人貴,一曲菱歌敵萬金。 「給他吃顆定心丸。
果然,得到張籍宣傳和引薦的朱慶餘,一舉考取了進士。他們的酬答詩永久地流傳了下來,成為後人賞拔人才的絕佳範本。
張籍想的很簡單,我只是做了當年老師為我做過的事。
作者:小安,本文經作者授權發布。 歡迎追蹤我的標題:少讀紅樓,為你講述不一樣的名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