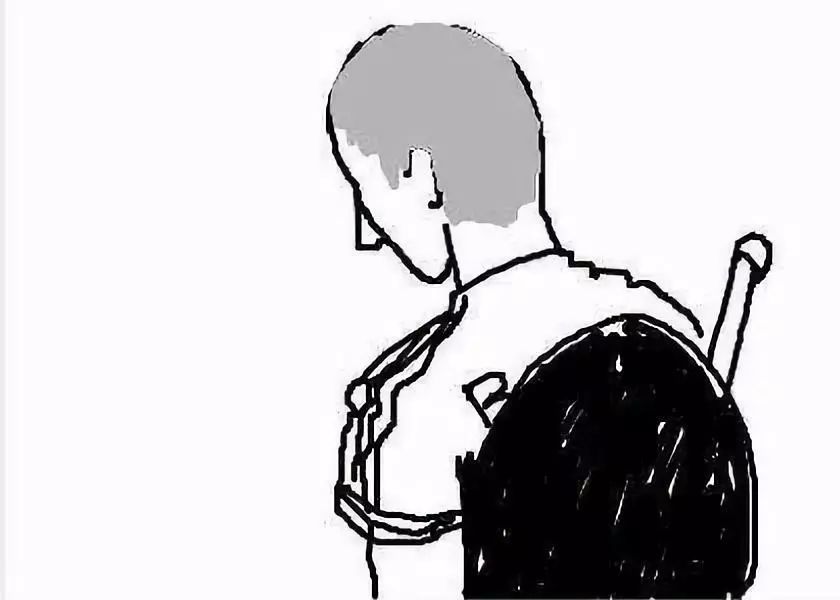
郭子儀去為死太監魚朝恩背鍋,兵權被奪,倒是李光弼被抬到天下兵馬副元帥的高度;而在大燕這邊,安慶緒被史思明一刀切了,正所謂皇帝輪流做,今年輪到我老史。當朕的感覺,還不是美滋滋?
內部整頓完畢,重新開戰。史思明大軍壓境,逼近洛陽。而大唐呢?忙著扯皮呢,幾個月前剛打了個大敗仗,鍋子儀背鍋去了,理論上資格最老軍功最盛軍階最大的,是李光弼。但問題在於,身為領導的李亨樹立了一個好榜樣,他用事實告訴各位軍區司令,誰說話都不算,除了死太監。而這回要命的是,連發號施令的死太監都不存在了…
眼看亂哄哄亂成一鍋粥,李光弼也是沒辦法。得,我說話沒人聽對吧,洛陽不要了。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政治不正確的做法,畢竟洛陽是東都,是大唐的經濟中心。只是話又說回來了,不要洛陽並不等同於一潰千里,老李的戰略是地留人存,讓彼此不服的軍區司令們外圍打遊擊,自個兒坐鎮孟津,還打了追擊的史思明一個埋伏,斬獲不少。還別說,這招相當管用,畢竟打又打不了,抓又抓不著,輪到史思明被動了。

怎麼辦?史思明眼珠子賊溜溜一轉,計上心頭,四處散播流言表示“河北弟兄想家啦,不想再打仗啦”,這與當年秦趙長平之戰的套路如出一轍,秦國散佈流言聲稱“廉頗老而昏庸,秦國只怕趙括”,結果一波送頭40萬。這回,智商捉急的魚公公再度信以為真,多次上奏李亨表示「是時候展示真正的技術,給史思明點兒顏色看看了」。李亨沒主見,允諾。一來李亨對魚公言聽計從,二來先前就說了,洛陽是東都,是經濟中心,長期落在叛軍手裡,也不是個事兒。
詔令下達,催促李光弼出戰。李光弼是個狠人,梗著脖子抗命,反過來勸誡李亨「現在就不是出戰的時候」。李亨這火啊,尼瑪我是皇帝你是皇帝?老子說話還算不算了?居然還找理由,不就覺得人手不夠嗎?來,老子把僕固懷恩也調給你,這回人夠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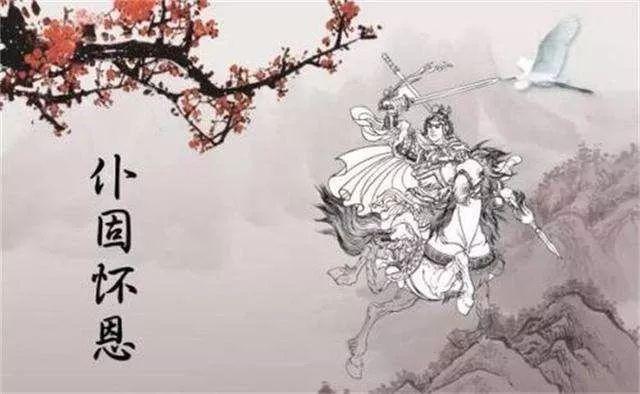
僕固懷恩是什麼人?這哥們是個非常傳奇的人物。論功勞,算是安史之亂的第三號功臣,僅次於郭子儀與李光弼。而且聽名字就知道,僕固懷恩乃並非漢人。這就是大唐制度先進所在了,能令少數民族同胞產生認同感,並為大唐盡忠。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僕固懷恩一家老小陣亡46人,算得上滿門忠烈,還為藉兵回紇犧牲女兒和親……但就是這麼一位大忠臣,卻在生命最後關頭扯旗造反,歷史之複雜多樣,由此可見一斑。
言歸正傳,僕固懷恩調來的本意是好的,加強李光弼的戰力嘛。但偏偏僕固懷恩與李光弼之間有仇,結仇的原因也不復雜,李光弼行事風格很跋扈,獨斷專行。巧的是僕固懷恩也是這路子。事實上縱觀僕固懷恩的軍事生涯,這老哥只對郭子儀服貼帖。兩個性格類似的人湊一起,當然不可能形成互補。更有趣的是,李光弼與僕固懷恩的軍事路線截然相反,李光弼擅長防守反擊,謀而後動;僕固懷恩則是進攻進攻再進攻。舉個不恰當例子就是──——
李光弼類似二戰時德軍防守大師莫德爾,而僕固懷恩自然就是隆美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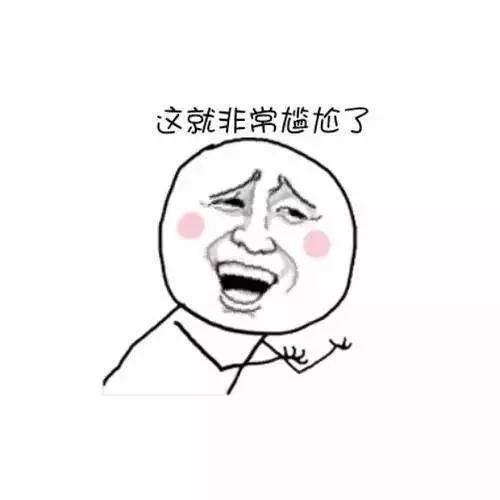
僕固懷恩都來了,李光弼只能出戰了。名義上,僕固懷恩要聽李光弼的,但僕固懷恩表示我聽個鳥。於是兩人又和鬥雞似的掐上了,李光弼表示要打野戰可以,山地列陣為好,這樣才能穩如防禦塔;僕固懷恩一聽就不樂意了,「慫逼悵成這樣還打什麼? 」堅持平原列陣。原本李光弒官大一級,可惜僕固懷恩背後有魚公公撐腰。爭來爭去死活沒爭出結果,史思明不耐煩了,表示也別吵了,送哥幾個一程。這一仗,史稱邙山之戰。
沒有任何意外,大唐又被打的屁滾尿流,萬幸的是這仗只是擊潰戰,而非殲滅戰,要不然長安還能再丟一回。當然仗打輸了一定要有人背鍋,誰背鍋?必然是僕固懷恩啦,誰讓丫非得堅持平原列陣的?至於僕固懷恩幕後老闆魚朝恩……別傻了,公公是不可能背鍋的,這輩子都不可能的。

平叛工作再一次進入到僵持階段,李光弼與史思明就大眼瞪小眼。一個喊“有種你過來”,另一個回應“有種你過來”。 《劍橋中國史》曾表示“如果史思明活蹦亂跳多活幾年,真有可能推翻大唐。”
平心而論,這話有點誇張,但平叛工作不容樂觀卻是實打實的。一方面史思明確實能打,另一方面叛軍有主心骨,武德充沛,士氣旺盛。按照正常的節奏,大唐想要徹底平定叛亂,大概還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然而,一個任誰都意想不到的變故再度發生,為這場已經歷經差不多6年的大動亂,標註了一個巨大的驚嘆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