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黃易,不得不說他開創的「奇幻武俠」。
蔡駿說他「以武俠入歷史,以歷史入幻想」;
六神磊磊評他「黃易之於武俠,就像是唐詩到了晚唐;黃易之於玄幻,則像是溫庭筠之於宋詞」;
自媒體葉克飛說出了許多讀者的心聲:“後來者學了他的穿越和情色,卻學不來他的天馬行空。”
簡言之,他是武俠的求變者、奇幻的開路者。追根溯源,網路中文寫作世界裡的許多體裁,都從效法黃易開始。穿越自不必說,男主角自備吸粉功能,一個龍騰虎步便可迷倒千萬美女,大多是學自黃易。
黃易2017年4月辭世,許多人嘆道「人間今覆雨,天堂再尋秦」。今天研習君蒐集整理了黃易前些年創作《封神記》時接受媒體的採訪,談到很多關於腦洞創作的心得,大家可以好好品味品味。

談創作:我的策略是「由短入長」
Q:談到您的小說,一些非議不得不提,例如其中的情色內容,最著名的便是《尋秦記》,為什麼要這麼寫呢?
A:作者在小說裡寫什麼?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我少年時看武俠小說,很愛看男女情事的描寫,但往往是點到即止,變成我的一個情意結。為什麼不可以把界線推過一點呢?或許基於這個心態,加上點實驗性的精神,我在《尋秦記》對男歡女愛有更深入的描寫,但從來沒因此後悔。
不過這只是某一創作階段的心態,後來就不想重複,修訂的時候更將這些部份刪除,提供另一個選擇。較著重情色的描寫只出現在《大劍師傳奇》《覆雨翻雲》和《尋秦記》內,反映著我的創作上近五年的心態歷程。
Q:您曾經說過,自己每次寫出來的作品,只跟之前的自己比較,希望有突破。您現在仍在尋找這個突破,還是已經有了答案?
A:“我只會視自己為唯一的對手”,乍聽似乎是目無餘子的狂言,實際上則是創作的一種方便,令你不會重複自己,有新的意念才有新的動力,挑戰自己,不住創新。
以我最新的兩部作品為例,在《雲夢城之謎》,我結合了遠古的神話和武俠,故意模糊歷史,對前世今生、命運做出深思,希冀找出一種全新的小說美感。
《封神記》則是延續《星際浪子》的精神,但跨出的步伐更大更遠,嘗試開創中外沒有任何小說曾觸及的題材,將科幻和武俠做出我認為最完美的結合,寫的是人類被滅絕一億二千萬年後,最後一個人類如何縱橫宇宙和宇宙之外的故事。是否突破?交由讀者做出判斷好了。

Q:讀者看您的作品經常會產生共鳴,故事發生在古代,但感覺與現在的事情很相像。您是有意把當下人面臨的問題和困惑寫進去嗎?
A:小說創作是沒有任何拘束和限制的,把小說的時空安置在歷史裡某一波瀾壯闊的時段,為的是與那個時代的政經文化結合,就像一艘遠洋船定下起點和終站,至於在航程裡發生什麼事,則可任由想像力做天馬行空的構想和深思。
最重要是能否創造出一個自圓其說的動人天地。 從這個角度去看,小說是可以無法無天的。我並沒有蓄意把當下的事物寫進小說去,想到便寫,創作的動力實令人難以節制和保留,有時小說自身的生命張力會反過來控制創作它的人。
Q:如何看待讀者對作品的批評?聽說《邊荒傳說》裡面,您把卓狂生寫成自己,反擊全世界攻擊自己的人。當初設定這樣一個角色,是想發洩自己對一些錯誤批評的不滿嗎?
A:我想沒有作者能不把讀者的評價絲毫不放在心上,我也不例外。褒嗎?自是甘之如飴;貶嗎?米已成炊,不開心白不開心,只好看看將來有沒有可改善的地方。
卓狂生嗎?罪過罪過,由自已去反擊批評並不適當,那完全是一種小說的手段,是在寫作過程某一時刻的靈機一觸,讓小說的人物與現實世界巧妙地結合,娛人娛己,其目的不在反擊,而在過癮。照道理,不喜歡看我小說者,當然對我小說避之則吉,理該聽不到狂生之言。

Q:您原來說《大唐雙龍傳》至少要到100卷,但卻戛然而止。很多喜歡這部作品的讀者都在推測其中的原因,請您先給解釋一下原因吧。
A:這就是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在創作《大唐雙龍傳》的某一階段,我確曾奮起這般的雄心壯志,然而小說有時也像歷史般,自有其因果發展的軌跡,不因人們的主觀意志而轉移,小說本身的生命力毫無疑問左右著篇幅的長短,硬要拖下去,我寫得辛苦,讀者看得不爽。
Q:您的書裡,愛情的成分相對少,友情的成分多,書裡環境險惡而缺少金庸作品裡的俠骨柔腸,但多了兄弟間並肩作戰的鐵血豪情和惺惺相惜……您更最醉心於兄弟之情的表達?
A:如果你指的是“篇幅”,那該是對的。投放篇幅的多少,純粹看劇情所需。以《大唐雙龍傳》為例,描述整個大時代的遷變,內則帝國崩潰,群雄割據,外則西域強鄰鷹瞵虎視,要刻畫寇仲和徐子陵從闖蕩江湖到縱橫中外的英雄功課,投放最多的篇幅是必然的事。
但我卻不認為「愛情」在我書中處於次要的地位。 說到底,小說寫的是人,與人有關的一切,人與人間錯綜複雜、恩怨糾纏的關係,都是我試圖表達的東西。
Q:您小說的框架總令人佩服不已,大都是勾勒一幅宏大的歷史性畫卷。這種架構小說的能力是不是也需要經常訓練?
A:我的策略是“由短入長”,先寫短篇、中篇,到有把握和信心,才著手長篇。 這和寫畫相似,初學畫時老師怎也不會教你由幾公尺長闊的大畫開始吧?這可視為一個學習的進程,也可視為訓練。當然可以有例外,不過我的情況確是如此。

Q:在創作中,由情節帶著自己走,是很快樂的事吧?是不是比較常常會有控制不住情節之感?
A:精確點說,該是當作者投入自己創造出來的天地裡時,每個情節、懸念,都會影響小說後來的發展,形成小說本體生命的張力,又反過來影響思路,是最自然不過的事。
快樂嗎?我會隨著小說的高低起伏、悲歡離合而心生變化,苦樂隨之。 寫小說或可以馴馬來說明,先要看你選上的是怎樣子的馬,如果是凶悍難馴的野馬,那就要考你馴馬的技術,給拋下馬來跌個腰折骨痛,當然難以為繼。要跑畢全程,必須慎選你力所能及的馬,成敗則交由讀者判斷了。
Q:您欣賞Bob Dylan,聽他的音樂或看他的歌詞,會刺激你的創作靈感,可以具體說說麼?除此,您的創作靈感常從何而來?
{不} {/不}
A:在我心中,Bob Dylan是當代的西方詩仙,其啟發性與我看唐詩宋詞類同,卻更貼近我們的生活,配上音樂打鑼打鼓以他獨特的唱腔道出來,更是藝術性娛樂性兼備。
我試譯他一段曲詞:「我遇上一個占卜師,她告訴我小心被雷劈,我久未嚐過和平安靜,久遠至令我早忘掉了那是怎麼一回事。有個在十字路獨自徘徊的士兵,他的盒裝車正在冒煙,但你不知道的是,沒有可能的事發生了,當輸掉了每場戰爭後,他終於取得最後的勝利。做著如此離奇的白日夢。 Wind, Blood On The Tracks)
當你聽過數以百計同級數的歌曲後,對創作怎都該有點幫助吧! 靈感來自生活和經驗的總和,心境更重要,那是「靈感之母」。

棄畫從文:找準自己的天賦與道路
Q:您在香港中文大學學的是國畫,你棄畫從文是基於怎樣的考慮?
A:我放棄國畫,在於某一刻的明悟,此事詳細記述於一篇有關我老師丁衍庸名為《午覺冊》的文章裡,我在親睹他寫畢畫冊後,這樣寫道︰「我曾經盲目相信自己有當個出色畫人的料子,但在那一刻卻清楚明白自己永遠不能做到像丁公那樣的藝術家。成材的小徒的未來。
Q:在您的小說中,涉及天文地理、風水歷史,包羅萬象,興趣相當廣泛,您是如何讓自己迅速了解這些知識,運用於小說並使人信服?
A:讓從頭說起。在大學期間,我對靈性修行生出興趣,學習瑜珈和冥想,又看了很多啟蒙老師介紹的書。
畢業後,對這方面的探索從沒有停過,閱讀的範圍應著視野的擴闊不斷開展。 我還有很多其它師傅,繪畫、古琴、洞簫、太極拳、掌相、子平八字、風水、道術。玄學和科學的知識,須是長期浸淫,沒有一促即就這回事。

談寫境界:武俠小說的真義在於打破平凡
Q:您一開始寫小說就呈現出與以往武俠截然不同的觀念,這種風格、題材的確立是經過怎樣的思考?
A:我最尊敬的兩位武俠小說大師是金庸和司馬翎,而我受司馬翎的影響又較大,從很多方面都可看到他的影子,當然,再加上我自己的東西,便成我現在小說的風貌。
對一位作者來說,一旦進入小說創作的天地,宛如踏入少林寺的木人巷,施盡渾身解數才有機會過關,必須隨機應變,不能只墨守師傅傳授的那一套。 而做人要謙虛,創作則須信心十足,所以打開始我便不得不信心十足地上路,因為根本沒有退路。
Q:您研究過儒道佛玄各種思想,最終玄學是你作品的思想基礎。為什麼你當初就認為玄學思想最能對讀者產生影響?黃易的筆名是否也與此有關聯?
答:愛思斯坦說:「最美麗的經驗,就是經驗玄秘,而這亦是所有真正藝術和科學的精粹。」於大多數人來說,要在日常的平凡瑣碎裡追求不平凡,於是我們各師各法,愛情、旅行、玩樂、看書、看電影,為的是從平凡沉悶裡破圍而出,活出生命的姿采。
但試問有什麼比神祕的事物在眼前發生更令人震撼?例如一艘外星飛船在你眼前下降。玄秘的經驗,或許只有當伽理略首次發現地球並非宇宙核心又或愛恩斯坦悟通對論的一刻。
武俠小說的真義,正在於打破平凡。 黃易的「易」字來自「日月為易」的易經,那倒是儒家的經典。

Q:像《尋秦記》《大唐雙龍傳》《覆雨翻雲》都是超長篇作品,常常百萬字之多,不知道您寫小說的習慣如何?是先有主線再一氣呵成,還是有了靈感再動筆?另外,寫作節奏加快,會不會導致人物和語言的單一化?
答:寫小說宛如沒有特定目的地的旅行,大致定下方向便起程,沿途柳暗花明,一切隨著小說自身的生命力拓展。我試過連續三個月每天都寫近萬字,那是我寫作速度的極限,回想起來仍感可怕。寫出來的東西,當然及不上身心悠閒時的水平。
談人物:仍在做「封神夢」
Q:您最喜歡您作品中哪位女主人公,為什麼?
A:這是個很難有肯定答案的問題,勉強來說或許是《大唐雙龍傳》的羈羈。 「愛你恨你,一生一世」,有寇仲和徐子陵這兩個難得的對手,又是愛恨難分,盡夠綾綹的生命發光發熱。我以「白衣如雪,裙下赤足的她牽著叫明空的小女孩,逐漸沒入雪花迷濛的深處」做全書的終結,絕非偶然。
Q:您最想成為您作品中哪位男主人公,為什麼?
A:肯定是《封神記》的伏禹,那種失去了所有同類的哀傷、孤獨,那種做任何事都沒有意義的沮喪,卻必須形單影隻的亡命宇宙,於沒有可能中找尋那可能性,使我迷醉其中,到今天仍做這封神夢。
Q:您喜歡金庸和司馬翎,請分別評說下金庸、司馬翎書中的“俠”,和您自己書中的“俠”好嗎?
A:我看書是偏向直覺和感性,只要能引人入勝,我會廢寢忘餐的追讀,關鍵在小說描寫的人物是不是有血有肉,可否引起共鳴。
至乎感同身受,金庸也好,司馬翎也好,總是在不同的小說框架內借情節的編排刻畫人性,各有各的體會和表達,亦各自精彩,很難做出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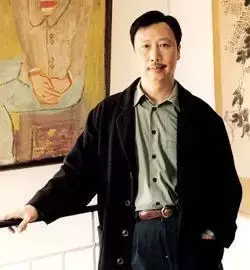
是的,比起金庸、梁羽生一代俠之大者,黃易更適合、也一直在做一個極具誘惑力的說故事者。找準自身定位,不斷用自身所學、所長豐富擴充所寫,窮極想像力的極限求得類型的突破,卻又比誰都明白讀者想要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