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什麼最惱人?蚊子排得上前三! 擾人清夢、其癢難耐,甚至還會傳播疾病。說它「人見人恨」絕不冤枉。
這隻讓人恨之入骨的“小蚊子”,至少從東週開始,就已經逼瘋古人。平日里,溫文爾雅的“士大夫”們,碰到這隻“小蚊子”,也束手無策。
堪稱「秀才」遇上蚊子,有理也說不清楚。 除了蚊帳和蚊香,文字成了詩人們少數的「解恨」工具。因此,蚊子,這隻既不好看,又害人的生物,竟然也是古人「詠物」詩文中的常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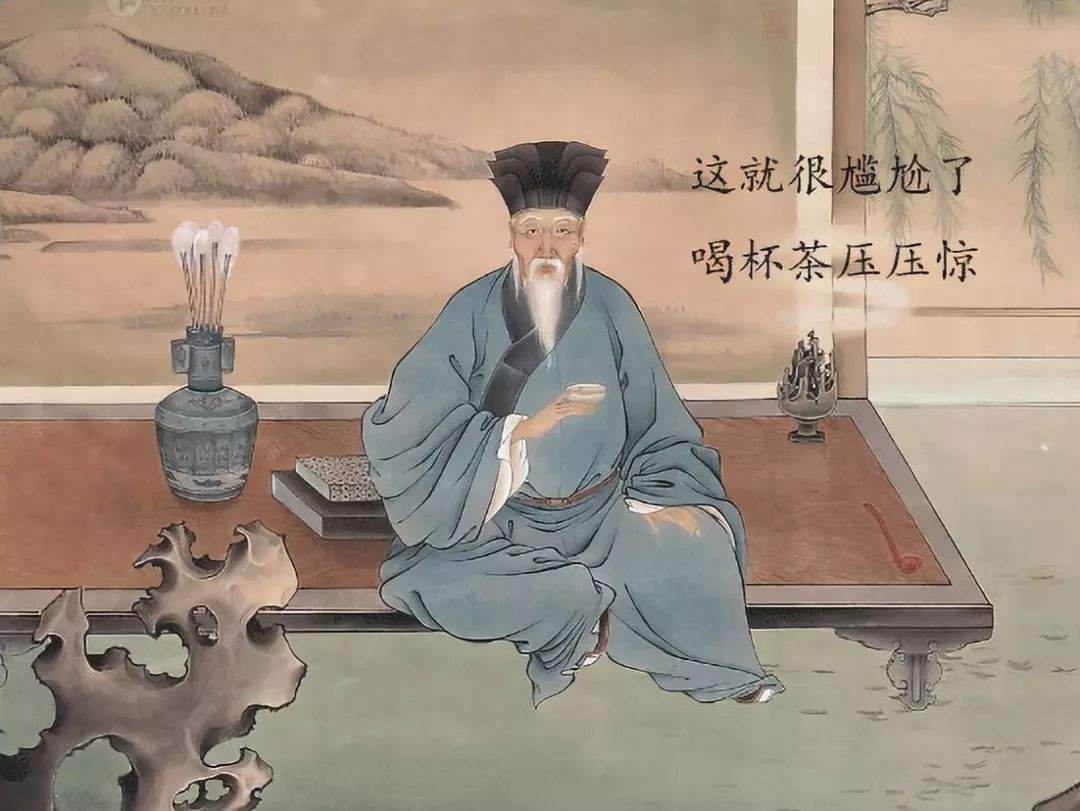
「大詩人」們不光夏天寫,冬天也寫。不光寫詩罵蚊子,也寫詩「分享」驅蚊妙方,甚至借蚊子罵人洩私憤。這其中,有些詩人“怒髮衝冠”,也有些詩人“佛系談定”。 一長串詠蚊詩詞梳理下來,眾人有眾相。詩詞中的詩人“滅蚊記”,也是“人間百態”的一面。

怒罵的“檄蚊詩”
被蚊子咬了,第一個反應是「怒」。包括大詩人在內,凡人是如此。 詩人們在文中,痛斥蚊子的三大罪狀,一是叮咬人體,影響睡眠和休息;二是善於隱蔽和攻擊,難以防範;三是傳播疾病,致人死亡。

白居易
蚊子的叮咬和聲音,幾乎讓大部分詩人崩潰。早在《漢書》就有「聚蚊如雷」的說法。類似的說法,不絕於後世詩詞中。 「動聚眾而成雷」(晉代文學家傅選《蚊賦》)也好,「噆膚不知足」(唐代詩人皮日休《蚊子》)也罷,抑或是「江邊夜起如雷哭」(唐代詩人韋楚老《江上蚊子》),蚊子的聲音已經讓詩人們抓狂,更不要說叮咬吸血了。
大部分詩人都有被蚊子叮咬得一夜無眠的慘痛經歷。唐代詩人白居易就因為被叮咬之後以痛止癢太過用力,到了「如有膚受諫,久則瘡痏成」這般遍地鱗傷的地步。就連老子這般高士也不能倖免,感嘆:“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
此外,蚊子善於逃避和攻擊的習性,也讓詩人們束手無策。 唐代詩人吳融發現平望地區的蚊子“不避風與雨,群飛出菰蒲。擾擾蔽天黑,雷然隨舳艫”,驚嘆蚊子比毒蛇和毒蟲還厲害,因為至少人還可以躲避蛇蟲。
大詩人蘇遼還在詩中提到了一種最兇猛的「豹腳蚊」。 當宋孝宗讀到蘇遼的那句“溪城六月水雲蒸,飛蚊猛捷如花鷹”,好奇心發作,還命下人抓了幾十隻豹腳蚊來探一探究竟。
最讓大詩人們害怕的,則是蚊子的「毒」可以致人死地。因為古代醫療衛生程度欠佳,常會出現因蚊子叮咬而病死的案例。就連大詩人歐陽修也感嘆道:“雖微無柰眾,惟小難防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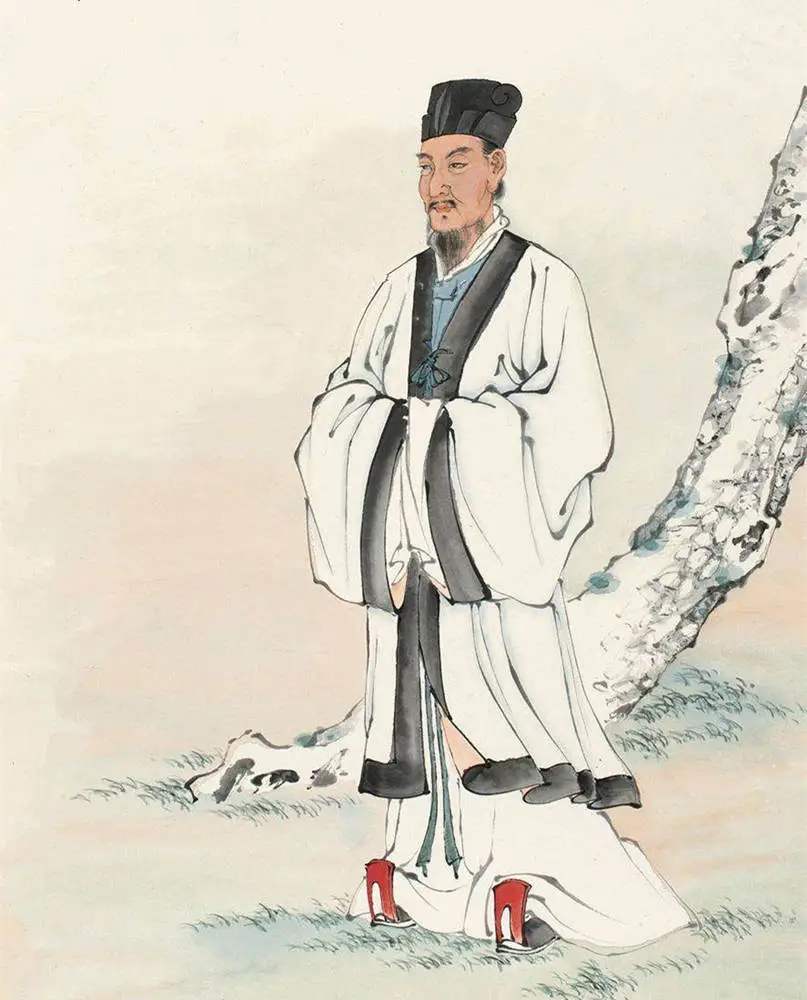
韓愈
不過,怒罵聲中,竟也有一些詩人比較佛系、淡定,不懼蚊子的叮咬和痛癢。 例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就說:「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秋天一到,一隻不剩,就讓它們去吧。
最有情懷的,則要數詩人孟郊。 他為天下人被蚊子逼瘋的情形,竟然說:「願為天下幮,一使夜景清。」意思說,我願化身為蚊帳,好讓天下人睡個安生覺。
如此“大義凜然”,實屬例外。南唐詩人楊鑾就因為對蚊子太過佛系,入選《全唐詩》的。 「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夜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鑾。」這首《即事》,也就成了楊鑾留名歷史的唯一一篇作品。

暗諷的“詠蚊詩”
“大詩人”和“小蚊子”,基本上是憎惡與被憎惡的關係。由此及彼,蚊子,也成為了古詩中「借喻暗諷」的主要對象。

劉禹錫
有藉蚊子,暗諷宵小之輩為害的。 例如宋代詩人趙雲松《憎蚊》一詩中寫道:「一蚊便攪人終夕,宵小由來不在多。」宋代詩人宋謙父還在《詠蚊》詩中諷刺趨炎附勢、朋比為奸的小人,終將惹來殺身之禍:“朋比趨炎態度輕,禦人口給屢憎人。雖然暗裡能鑽刺,貪不知機竟殺身。”
有借蚊子,諷刺小人趨炎附勢的醜態的。 例如夏原吉《詠蚊》抓住了蚊子喜熱怕冷的特點,以諷刺趨炎附勢的小人:「白露鑲壤木葉稀,痴蚊猶自傍人飛。信伊只解趨炎熱,未識行藏出處機。
更多的詩人,是藉蚊子諷刺政局昏暗、表露堅毅內心。 例如大詩人劉禹錫有一首《聚蚊謠》,寫道「我軀七尺爾如芒,我孤爾眾能我傷」就是一種暗諷。前文提到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癒的那句:「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諷喻的意味也比較明顯。

影視劇中的馮夢龍。
還有一些詩人,把蚊子喻為商人、妓女、惹事生非之人等。唐伯虎曾為商人寫了這樣一副對聯:門前生意,好似夏日蚊蟲,隊進隊出;櫃裡銅錢,要像冬天蝨子,越捉越多。以此諷刺市儈的庸俗和貪婪。 馮夢龍編的《掛枝兒》卷八中,就有一首以蚊子隱喻妓女的小曲兒:「蚊蟲兒,生就你惺惺伶俐,善趨炎,能逐隊,到處成雷,吹彈歌舞般般會。輕嘴兒專向醉夢中討便宜。
同是《掛枝兒》卷八,還有一首詠蚊小曲訌的是多言亂說、惹是生非之人:「蚊蟲哥,休把巧聲兒在我耳邊來攪諢,你本是個輕腳鬼,空負文名,一張嘴到處招人恨。
借蚊子諷刺貪官、小人、妓女、惹是生非之人、市儈之人等等,足見被蚊子「迫害」的大詩人們,對這隻小小生物是多麼深惡痛絕了。

驅蚊的“科普詩”
一些詩人,感性佔上風,怒髮沖冠,用文字痛罵“蚊子”權當洩憤;也有一些詩人,較為理性,通過詩文分享滅蚊、驅蚊的妙招,目的是“殺之而後快” 。
例如,大詩人歐陽修的好友梅堯臣,就曾在《和江鄰幾景德寺避暑》一詩中分享了用艾驅蚊的效果: 「枕底夕艾驅蚊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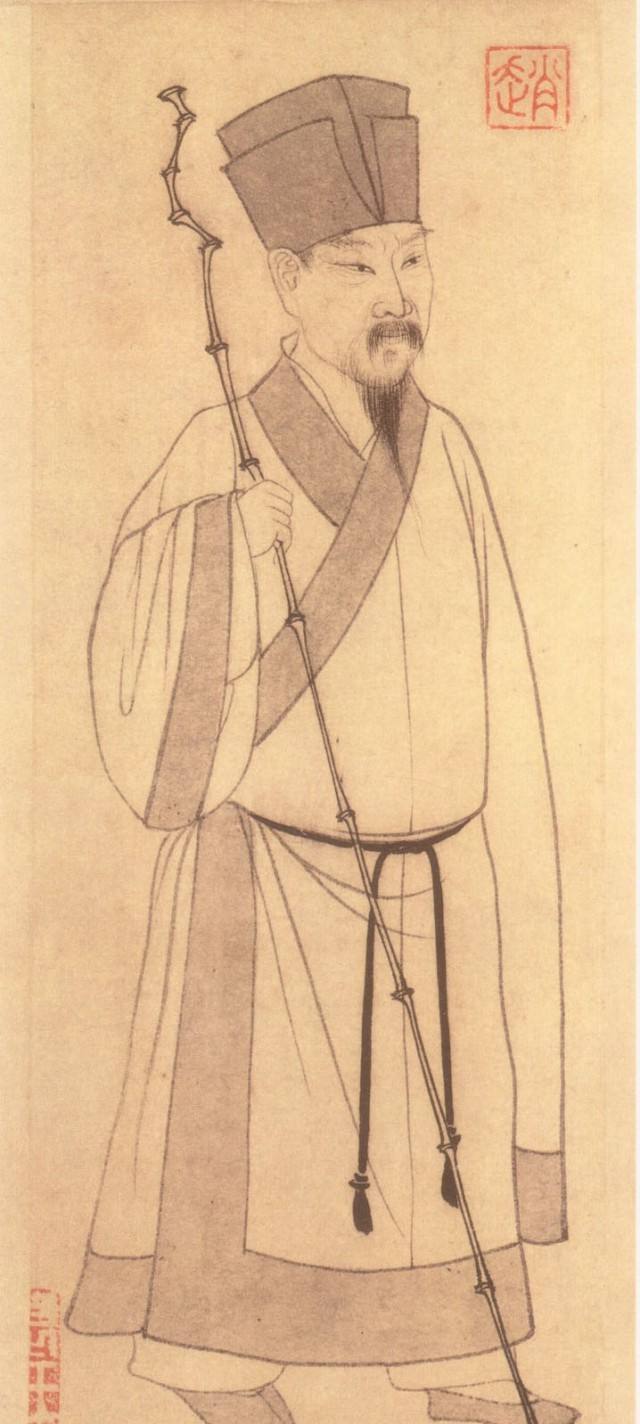
蘇遼
為了推銷“蚊香”,古人甚至借大詩人蘇遼之名寫“軟文”。 宋代冒蘇遼之名編寫的《格物粗談》和《物類相感志》就分別幾個「蚊香」配方。例如,「端午時,收貯浮萍,陰乾,加雄黃,作紙纏香,燒之,能祛蚊蟲」;「水中浮萍,幹,焚煙燻蚊蟲則死」;「麻葉燒菸能逼蚊子」等等。
不知道,這些“軟文”,是不是中藥販子瞅準了巨大的“蚊香”市場空白,而為了推銷產品而寫的呢?
「大詩人」和「小蚊子」的這一段趣事,真是應了那句:「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或許,我們再也找不到一個比蚊子更豐滿的形象,負擔了人類心中那麼多的憎惡、惱恨以及無可奈何。
我們已和蚊子在詩歌中同處幾千年,我們依然還要與之繼續共享這個人世間,真是令人又皮癢、又頭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