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墨子的宗教思想,主要表現為天志和明鬼。我們先來看他的上帝鬼神觀。天:「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溪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是自然的主宰者,秩序的規定者,百物的賜予者,萬民的厚待者。由此可見,墨子對天的理解與《尚書》、《詩經》中的記載是一致的。天亦稱為上帝。 「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國家的政權、君長皆為上帝所立。 「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上帝無私、德厚、聖明,是全知、全能、全善的至高神明。 「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既然上天是善之始,利之源,當然希望人相愛相利,反之則施以懲罰。 “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總結為一句話:“天欲義而惡不義。”

在墨子看來,「義,利也。」(《經上》)義利是一致的,具體表現在施政上:「義者,善政也。」他進而認為:「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為「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然後將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 「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正因為義是天之所欲,所以「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治是義的,治國以義為標準,是遵循天志的表現。 「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而上天的意願,是讓人和人之間互愛、互助、互利。
「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上天明察秋毫,賞善罰惡,對於王公大人和庶民百姓,一視同仁。就是貴為天子,也不例外。 「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之暴,天能罰之。」墨子舉夏商週三代聖王禹、湯、文、武和三代暴王桀、紂、幽、厲的例子作對比,說明上天福佑聖王、降禍暴王,賞罰分明。天意就是規矩和審判的準則。 「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員,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 。
墨子的天志思想,來自三代宗教中的“上帝”信仰。而明鬼思想,同樣源自三代宗教中對天神、地祇、祖先的崇拜。 “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為鬼者。”鬼神是上帝施行公正、賞善罰惡的使者。墨子引用《禹誓》、《商書》等古籍以及各國春秋史傳中的相關記載,說明鬼神對人間的監察和介入。 “昔者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與聖王們敬事鬼神相反,暴王們上不敬鬼神,下不恤百姓。 “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為了證明鬼神的靈驗,墨子舉了賢明的秦穆公在廟中遇神句芒,加壽數;觀辜因祭祀不虔敬,被附身於祝的神明殺於祭壇上;枉死的杜伯、莊子儀當眾向周宣王、燕簡公復仇的事例。表明鬼神作為上帝的使者,明察秋毫。不管是天子王公,還是庶民百姓,行善作惡,皆逃不脫鬼神的監察賞罰。墨子的鬼神觀,繼承了三代宗教中敬天尊祖的傳統。特別強調上帝鬼神公正嚴明,賞善罰惡的力量無所不在,所謂“抬頭三尺有神靈”,讓人因敬畏鬼神而揚善去惡。
2
只有理解了墨子的宗教觀,我們才能對墨家的人生觀有深入的體會。非命非樂是墨家人生觀的核心表達。墨子一方面篤信上帝鬼神,一方面否定宿命。在他看來,上帝並不預先規定人的命運。人的富貴貧賤、生死禍福,都是所作所為的結果。對於儒家的命定論,墨子概括道:“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智力,不能為焉”。孔子有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儒家的天命觀,帶有宿命的色彩。儘管孔子周遊列國,積極推行他的王道,但這只是君子在“知命”的前提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並非是要改變天命。而墨子之承認“天志”,徹底否定“天命”。 “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未嘗有也。”他認為宿命觀念讓人無所作為,百事荒廢。對王公來說“必怠乎聽獄治政”;對於大夫來說,“必怠乎治官府”;對於農夫來說,“必怠乎耕稼樹藝”;對於民婦來說“必怠乎紡績織絍”。如此一來,政治和經濟就會陷入癱瘓。三代暴王不事鬼神,篤信命定,將他們失去天下歸結為“我命固且亡”和“吾命固將失之”。以命定論為藉口,推卸國破家亡源於其不敬上天、不恤百姓的罪責。
墨子堅決否定「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的命定論,認為行善有福,為惡遭禍。但現實中,並非總是善惡有報,所謂「好人不長命,禍害活千年」的事例也不少。有一次墨子生病,他的弟子跌鼻在探望老師時,問墨子既然鬼神明察秋毫,賞善罰惡,像您這樣的聖人,怎麼會得病呢?是您的言語有過失?還是鬼神不明察?墨子回答說,得病的原因很多。天氣冷熱、勞累過度都可能導致得病,這就如同百扇窗只關了一扇,盜賊怎麼會沒處進來呢?墨子的回答,有一定道理。但並不能叫人完全滿意。跌鼻與墨子的對話,涉及「非命」論在解釋「德福一致」問題上的不足。其實,在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思維範式中,無論是儒道墨,還是諸子百家中的其他派別,都不能對此問題給出滿意的答案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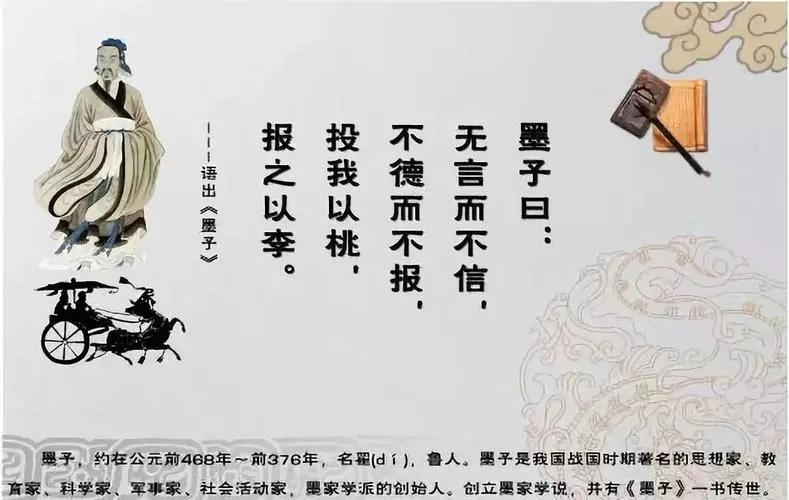
從「現世」來看,德福一致和德福不一的現象,是同時存在的。我們可以說,善有善報,時候未到。但是,現世報是有限制的。很多為社會做出巨大貢獻的人,在人世的結局不一定好,反之亦然。中國先秦的思想中,雖然不乏天地鬼神、道理性命等神秘觀念,但卻很少涉及「來世」。孔孟不言,老莊不語。夏商週的三代宗教中,雖有對祖先和鬼神的祭祀,卻沒有明確的「天堂」與「地獄」觀念。從墨家的鬼神觀來看,賞善罰惡都是現世報。中國人的「來世」觀念,是在佛教傳入後,才漸漸明晰起來的。在佛教中,彼岸福報與輪迴涅槃連結在一起,所謂極樂世界與無間地獄,對於信眾產生的激勵和威懾作用,是傳統三代宗教難以比擬的。與佛教複雜的輪迴轉生相比,基督教的「末日審判」更容易理解。信與不信,成為上天堂與下地獄的條件。中國本土的宗教信仰,受天人合一觀念的影響,來世和彼岸觀念淡薄。因此,活得更長,活得更好,成為“神仙”,甚至“只羨慕鴛鴦不羨慕仙”成為主導的思想。老子、莊子、列子、墨子都被附會成神仙,秦皇漢武迷信仙道,都是這種思想的表現。
墨子的生活態度,主要表現在「非樂」上,其指導原則是「仁之事者,必務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春秋戰國時代“禮崩樂壞”,音樂的主要功能已由周初的“享神”變為“娛人”。宗教意義淡化,世俗色彩增強。墨子看到當時戰亂頻仍,民不聊生。 「飢者不得食,寒著不得衣,勞者不得息。」而王公貴族們卻撞鐘、擊鼓、彈琴、吹笙、勞民傷財、醉生夢死。對社會上層來說,沉迷於此將荒廢政務,對社會下層來說,沉迷於此將懈怠生產。於國於家,有百害而無一利。這是從社會現實來說的,墨子也引用《武觀》、《黃徑》、《官刑》等古籍的記載,證明「聖王無樂」。
“非樂”思想的提出,並非是因為墨子“自苦為極”,而是與當時的不良社會風氣相關。 “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王公貴族、卿士大夫生活富足,過度消費,奢靡逸樂;農夫民婦、役夫工匠缺吃少穿,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在廣大民眾基本生活需求尚未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少數貴族卻追求所謂的高品位奢侈享受。朱門酒肉臭與路有凍死骨形成鮮明的反差,墨子大力提倡非樂,是對這種現象的批判。希望王公貴族們扭轉不良風氣,注重國計民生,體恤下層疾苦。
3
墨家「節用」的經濟思想,是與其人生態度一致的。同樣,墨子認為這是古代聖王的美德和施政原則。即「是以奉給民用,則止。」而「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由此可見,「節用」的主張和「非樂」一樣,也是為了限制統治階級和社會上層的鋪張浪費。具體來說,在飲食方面:「是以充實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昧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服飾方面:「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綹之衣,輕且凊,則止。風寒,上可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祭祀,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
「節葬」是「節用」在喪葬方面的具體應用,主要針對的是儒家厚葬久喪的觀念。所謂「三年之喪」的提法,並非三代舊制,而是儒家的主張。墨子認為守喪太久,人的身體會虛弱,甚至生病。耽誤王公大人、卿士大夫治理國家,耽誤農夫民婦農耕紡織,耽誤工匠製作用具。同時妨礙男女交往,減少人口。厚葬會浪費大量財物,不能為民所用。人口減少,貧病虛弱,會導致祭祀鬼神的貢品品質下降,抵禦外國侵略的兵源不足。於國於家,於神於人皆有害無益。墨家從當時的社會現實,尤其是生產生活、國家治理的民生、國防角度,提出集實用和有利於一體的經濟思想,讓統治階層將財物、精力多用在國計民生上,尤其註重民眾的健康和人口的增長。
4
墨家的政治主張,體現在尚同和尚賢上。在墨子看來,「尚同為政之本而治之要也」。並且特別強調:「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眾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尚同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從社會發展來看,由於每個人有不同的想法和慾求,「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沒有公認的是非善惡標準和社會統一秩序,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將大行其道,結果必然是人人彼此對立,互相加害。 「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
春秋戰國時代,大國兼併小國、家臣篡奪國位,戰亂頻仍、攻伐不止。墨家尚同的思想,為結束當時的亂世割據,建立大一統的和平局面,提供了方向。但是,“同一”合“統一”的標准在哪裡? “且夫義者,政也。”就是從正義的原則出發。 “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而“天欲義而惡不義”,由這個最高原則出發,尚同就是天子同於天,三公同於天子,諸侯同於三公,卿士同於諸侯,庶人同於卿士。即“無從下之政上,比從上之政下。”但是,墨家的大一統方案,並非回到周初的封建宗法制,與儒家強調的“親親、尊尊”大相徑庭。而是提出了打破血緣宗法和世襲等級的“尚賢”主張。其總綱為“以尚賢使能為政。”墨子認為這是先王的為政之道。 “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盤盂,傳以遺後世子孫。 」與儒家相似,墨家同樣法先王,追求明君賢臣的人治理想。不過,墨家特別重視在“貴義”前提之下的“公平”,與儒家“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廬人”不同,採取對團體內成員一視同仁的態度。人者刑」的規矩,大義滅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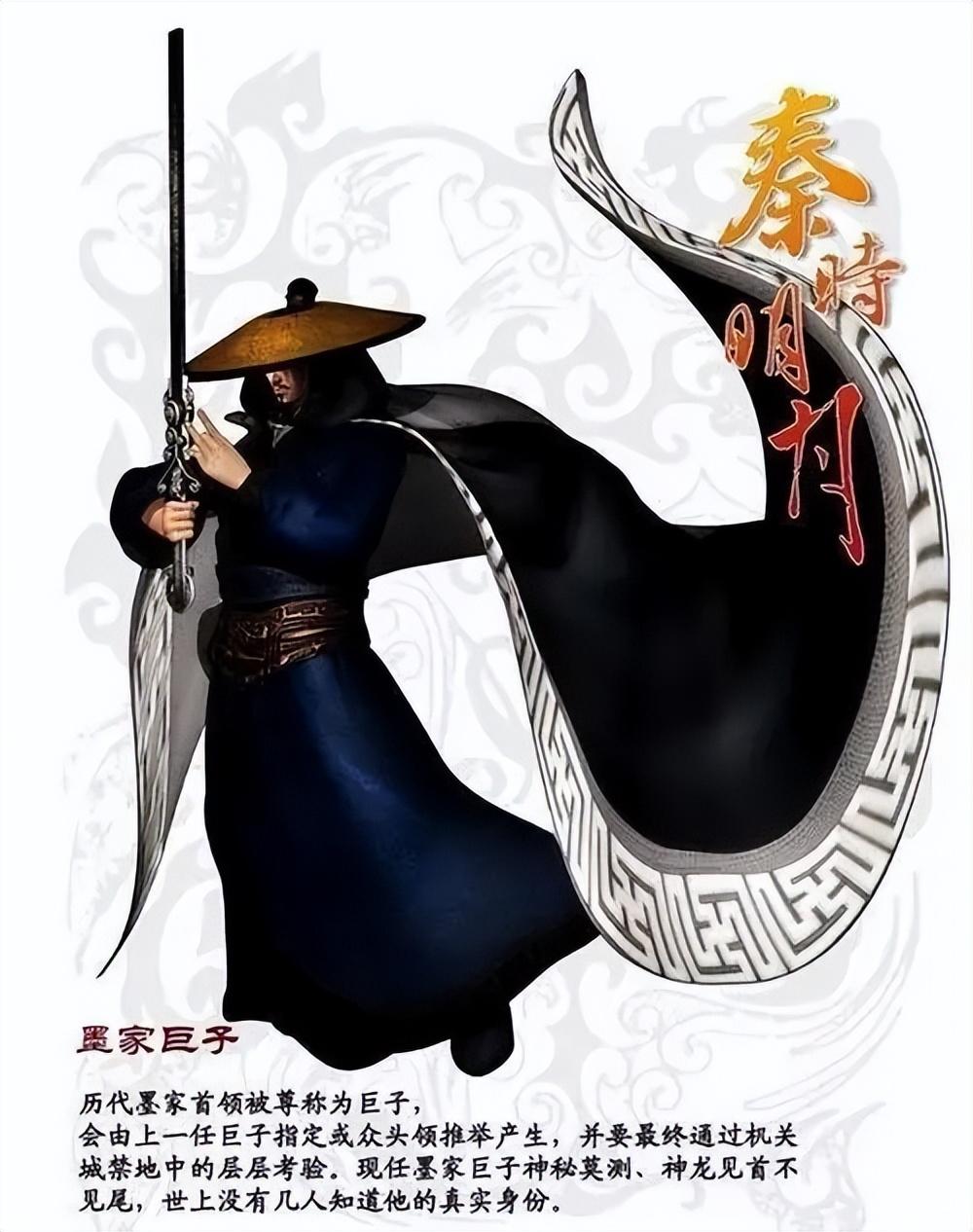
墨家團體具有“教會”的性質,奉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法紀嚴明,禁止徇私。在選賢以能的具體標准上,要求“里長也,里之仁人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也就是說,從最小到最大的行政長官,都是相應管轄區域內的賢能者。如此一來,就能夠保證“尚同”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不是建立在“親親、尊尊”的私人關係親疏遠近上,而是公眾認同的德行和能力上。 “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這是一種典型的“精英”治理觀念,作為被選為官者,一方面要服從上級的命令,“上是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同時,也有對上級提出意見的義務,“上有過則規諫之”。
龔自珍有詩曰:「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才的選拔和任用,最重要的是打破私人關係的障礙和社會分層的限制。墨子提出:「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充分體現了唯才是舉,唯能就任,按勞得賞,按功受祿的公平公正性。而且特別強調:「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的賢者不問出身的原則。墨子曾向楚惠王上書,惠王稱讚墨子的書很好,卻不願實踐其中的主張。墨子因此拒絕留在楚國,惠王派大臣穆賀為墨子送行,穆賀直言不諱地對墨子說,王或許因為你是一介平民,才沒有採納你的主張。墨子舉尚湯禮賢下士,親自拜訪伊尹的事例,感嘆草藥能治天子的病,糧食可以祭祀上帝,而他的主張在王看來,卻不如草藥和糧食。對於人才因出身低微而不受重視,墨子深有感觸。所以才大聲疾呼:「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可惜聽者寥寥,行之更少。
5
墨家的倫理思想,主要體現為「兼愛」與「非攻」。兼愛是原則,非攻特別針對當時殘酷的併購和侵略戰爭。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墨家的兼愛非攻主張,在當時具有理想色彩。墨子及其弟子後學,奔波於列國的主要目的,就是宣揚和平,阻止戰爭。墨子曾勸止楚王攻宋、魯陽文君攻鄭。鉅子孟勝與弟子一百八十三人,為陽城君守城而亡。在止楚攻宋時,墨子大膽指出:「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侵略戰爭,是不仁不智之舉。而公輸班作為楚國大夫「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身為國家要員和技術精英,魯班利用自己的發明推動戰爭,實謂不忠實之舉。墨子無情地揭露了侵略者偽善的假面。魯陽文君意圖攻擊鄭國時,以鄭國人弒君,天罰其三年不順為由。墨子一語道破其替天罰惡的虛假,好比一個父親拿著木棍,要教訓鄰居不成器的兒子一樣。真正的目的,不過是為了趁火打劫,對災難中的鄭國落井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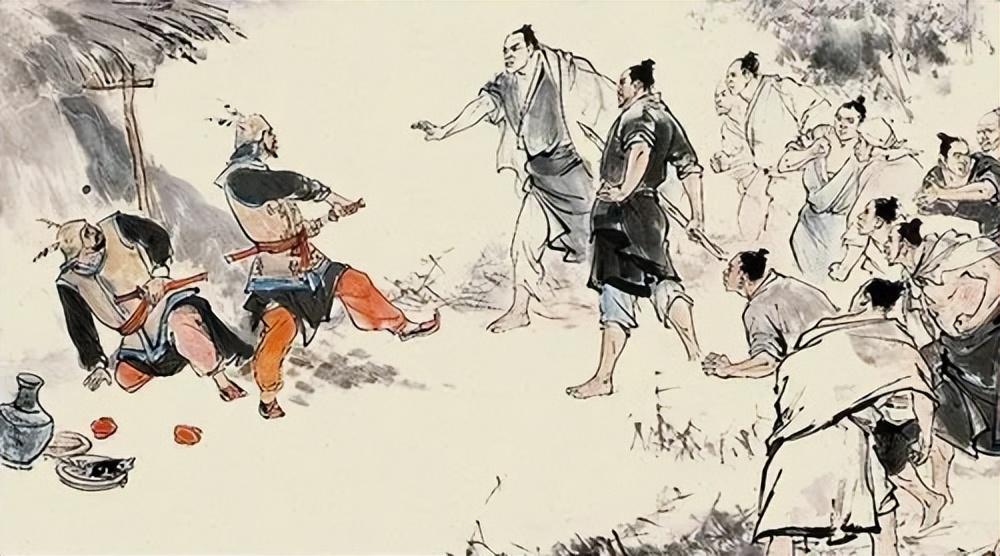
侵略者總是為自己發動不義戰爭,尋找各種冠冕堂皇的藉口,其實不過是恃強凌弱,強取豪奪而已。墨子在揭露侵略者偽善的同時,從現實的角度,說明侵略不僅會給被侵略的國家造成災難,對侵略者同樣有害無益。 “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侵略戰爭不一定能獲勝,即便勝利,也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由於侵略戰爭多由大國發動,墨子反對爭霸,倡導統一,並將之歸於先王之道:“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富之,人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兼愛非攻是天之所欲,聖王所行。而兼愛的原則是:“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概括來說就是:“為彼猶為己也”。這種一視同仁,愛人如己的思想,具有宗教信仰的色彩。同時,墨子也從人際關係的角度,提出“兼相愛”會帶來“交相利”的效果。即“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他引用《詩經》中投桃報李的典故,來說明這個道理,提出:“必吾先從事於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墨家倡導兼愛,就是先從愛他人做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