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他“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是繼孔孟之後,中國儒學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朱熹融合儒、釋、道三教,並加以時代的改造與創新,集宋代新儒學之大成,對中國後期封建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因而,他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有哪些著名的思想論斷?為何被評價為偉大的教育家?今日,讓我們一起了解朱熹傳奇的一生及對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事業的重大貢獻。
為官:「視民如傷」「以人為本」

朱熹出生於南宋初年,他天賦過人,“幼穎悟”,是個“逢考必過”的少年。朱熹18歲中貢生,19歲中進士,後來被任命為泉州同安縣主簿。
青年朱熹來到同安上任,就職之始,就在官署大堂上懸掛了一面「視民如傷」的牌匾。
「視民如傷」出自《左傳》中陳懷公與逢滑的一段對話,陳懷公問:「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意思是,國家被敵國戰勝,國君逃亡,這不是災害又是什麼?逢滑回答:「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意思是,我聽說國家想興旺,就要把百姓當作有傷病的人一樣照顧,這就是它的福德;國家想滅亡,就把百姓當作塵土草芥,這就是它的災禍。
朱熹初入仕途將「視民如傷」公開懸示於眾,不僅是一種為政宣示和對自己的提醒,更是以此接受百姓們的監督。 《宋元學案》記載,朱熹在同安任職期間體卹鄉裡百姓,上書減免賦稅,重視鄉村教育,籌款整修縣學。他政績突出,深受鄉民擁戴,3年任期結束,「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
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官名)。他到任時逢大旱,災情十分嚴重。朱熹不僅著手興修水利,抗災救荒,也積極向朝廷爭取減免稅賦。由於措施得力,百姓「多所全活」。這時,浙東地區也發生了災荒,朱熹因為救荒有方,朝廷命朱熹前往浙東救災。
朱熹還沒到任就給各地州郡寫信,召集米商,免除他們的商稅,等朱熹到達時,各地商船運來的糧食已經聚集了很多。朱熹每天都深入鄉間考察災情,《宋史》記載朱熹“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也就是在鄉村考察時一律單車獨行,不帶隨從,所到之處人們都不知道他的身份。他雷厲風行,也以此要求屬吏,有的官吏受不了而「至自引去」。對於丁錢、役法等規定,如對百姓不利,朱熹都整理出來加以革除,同時制定規劃,為百姓做長遠打算。朱熹在浙東雖然時間不長,但政聲遠播。
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受詔赴經筵講義,因此引起了權貴妒恨,皇帝以「朱子迂闊」為由,將在朝僅46天的「帝王之師」朱熹逐出禦前經筵。第二年,皇帝又聽信反儒道的朝臣諫言,將儒道視為偽學,下旨罷免朱熹祠職。
為師:將山水之美與教育緊密結合
朱熹仕途並不順利。一方面是因為他的父親是一名“主戰派”,得罪了朝中主和的權臣,朱熹多少也受到一些影響;另一方面,朱熹服膺儒學,平生有志於遊學、講學,對官場並不熱衷。朱熹從開始為官至去世前的50多年間,仕途經歷時斷時續,中間曾以各種理由辭官。

朱熹一生除了講學著述,很大一部分時間就去遊歷山水。他在書院或精舍講學近50年。期間只要一有閒暇,便去觀光踏青,遊山歷水。其遊歷興致之高,賞察之深,足履之勤,重遊之頻,可謂與生命相伴,成為其生命活動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內容,按他自己的說法就是他可以為此“足以樂而忘死」。
但他也不是單純縱情山水,而是將山水情懷與教育緊緊地連結在一起。宋代是我國書院教育體制的盛行時期,作為南宋時期發展理學的集大成者和鼎新書院的著名教育家,朱熹對中國的書院教育體制的發展和盛行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先後興復了著名的白鹿洞書院和岳麓書院,並創建了寒泉、武夷、竹林三所精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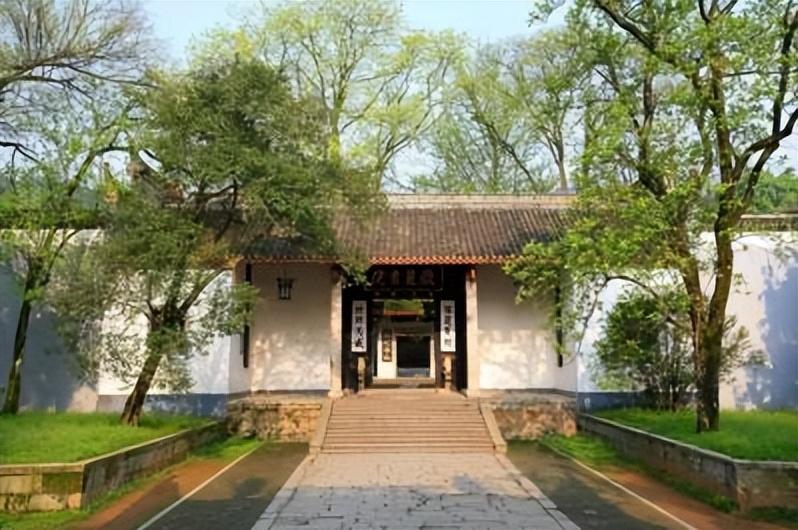
朱熹在建造書院時非常重視地點的選擇,不論白鹿洞書院,還是岳麓書院,朱熹將遊歷中發現的風景最優美的地方選作院址,這是個了不起的創舉。我國現代偉大的教育家陶行知指出:「關於籌備(學校)重要問題之一,即為校址之選擇;因為天然環境和人格陶冶很有密切關係。」而朱熹生活時代距今近千年,在當時已深知自然美的環境對受教育者的重要影響,並且努力為之,實為難能可貴。
朱熹自己在《武夷精舍雜詠詩序》做過詳細的記載,從中可見書院的創立,從環境地址的選擇、建築佈局的搭配、院舍堂室的命名,到生活設施的安排、講學氣氛的營造,都充分體現了“與造化俱遊”,與林泉共樂的山水美學情趣和人文精神。
治學:著有《四書章句集註》,
構築起龐大的哲學新體系
《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合稱《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集注》或《四書》,是朱熹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在宋代形成的中華文化新經典。
少年時,朱熹秉持先父遺命,拜「五夫三先生」劉子翬、劉勉、胡憲為師,研讀《四書》。 「五夫三先生」崇尚二程理學,對《四書》都有深入而獨特的研究,胡憲更是將長期收集的數十家《論語》解說,附以自己獨特見解而成的《論語會義》傳授給朱熹。此書為朱熹註釋《論語》提供很大幫助。
在他們教導之下,朱熹堅持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研究中心,研讀大量學術著作,為研究《四書》奠定了全面而紮實的基礎。

中華文化從遠古到孔子集大成,孔子後到朱熹集大成,是世界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孔子編撰《五經》,成為中華文化的初步原典。
西漢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五經》文化經典的地位,但回應不了當時社會思想需求和佛學道學的挑戰,導致孔子創立的原始儒學日益邊緣化。
中華文化發展到了關鍵時刻,在尊崇維護《五經》的同時,需要重新選擇意義更加突出、內容更加明確、能回應佛道挑戰的新經典。選擇新的文化經典的任務,從唐代韓愈提出,經北宋周敦頤、程頤、程頤、程頤、張載,最終落在了朱熹身上。
朱熹認為,《五經》內容豐富但表達的意義不夠集中、明確。他繼承二程從《禮記》中分出《大學》《中庸》兩篇的思路,並將《論語》《孟子》提升到「經」的地位,與《大學》《中庸》合稱《四書》,形成文化新經典。
朱熹用40年時間“遍求古今諸儒之說”,融匯百家,收集各種經典文本,加以研究註釋。 《論語集註》引用學者1629條註解,《孟子集註》引用學者1324條註解。在此期間,他也寫了《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大學解》《大學或問》《論孟精義》等與《四書》相關的著作,建構起包括理氣論、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理一分殊在內的龐大的哲學新體系。
作為文化集大成之作,《四書集注》視野開闊,理論深邃,從宋代開始普及,元代被定為科舉考試的教科書,由此也確立了朱熹在哲學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來源:微信公眾號「人民出版社讀書會」
編輯:倪傑(實習生)
【聲明:本號為「全民閱讀推廣」官方公益帳號,轉載此文是出於傳遞更多訊息之目的。若有來源標註錯誤或涉嫌侵害您的合法權益,請與我們聯絡。我們將及時更正、刪除,謝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