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從作家到文化遺產保護者

著名作家馮驥才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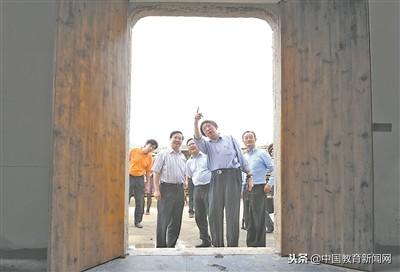
2015年7月,馮驥才研究蚌埠市古民居修復倉庫。他說:“古民居的保護有上千種方法,不要輕易否定任何一種保護方法。”

每當盛夏時節,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整體會被爬山虎包圍。院子裡有一處人工湖,裡面有很多錦鯉,馮驥常常來餵食,與魚逗樂。

馮驥才先生接受中國教育報記者陳欣然(左)和禹躍昆(右)採訪。資料圖片
這些畫都是我的心血,我喜歡我的畫,都不知道我把這些畫賣了是一種什麼感受。
原住民的文化自覺、村鎮管理者的文化自覺,完全都沒有,人們的眼裡只有利益。這是價值觀的問題,是需要文化自覺改變的。
初次造訪位於天津大學青年湖畔的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給人的感覺與其說它是研究院,不如說它是藝術品。
斜向架空的建築將一塊方正土地分成南北兩個楔形院落,一池淺水貫穿其間。如果恰逢盛夏時節,青磚鋪就的庭院中,爬山虎爬滿牆壁,花草樹木自由生長,水池中錦鯉遊來游去。走進樓內,藝術氣息撲面而來,明代石獅子、宋代天神像、各類字畫雕塑,以及從民間蒐集的藝術品等,讓人目不暇接。
在這所以理工科見長的大學的腹地,有這樣一方人文綠地,著實令人驚嘆。
2001年,以馮驥才先生的名字命名的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正式成立。從那時起,這位著名作家、畫家、文化學者,便在天津大學校園里扎下了根,按照他對教育和文化的理解,一點一滴地為這座學院添磚加瓦、充實血肉。而他自己對文學、藝術、文化、教育的理想,也在這過程中開出絢爛繁花。
沒有人文精神的教育是殘缺的
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成立於2001年,大樓於2005年建成,此時正值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全面鋪開,研究院順理成章地成為文化遺產搶救的學術支撐與人才基地。
在十多年的時間裡,馮騖才將教育科研與文化遺產搶救結合起來,借助現有的平台和珍存,將學術研討、教育講壇與各種文化藝術展演相結合成研究院特有的活動方式。同時,一大批學術研討成果也在這裡問世,如論文集《鑑別草根》《田野的經驗》《教育的靈魂》等,這些成果有的記錄了非遺的搶救與保護,有的收錄了教育家的思想與高見,具有很高的價值。
2006年考上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的王坤,在馮驥才門下攻讀碩士、博士,最後成為研究院的教師。由於研究方向是年畫,她也多次跟隨先生赴河南滑縣等地進行年畫方面的田野調查。王坤說:“在這一過程中,我從先生身上學到最多的是對文化的關切與敬畏,以及文化責任感與擔當。”
在王坤看來,馮驥才對學生們最大的影響是精神上的引領,他對許多文化現象的思考都深深影響著大家的行與思。他認為對學生來說,最重要的是思想、眼界,而不是知識,因此學生們都努力去理解他對文化的獨到見解,學著像他那樣,在浮躁的社會中沉下心來做純粹的、無功利色彩的學術研究。
對於教育,馮驥才有自己獨到的理解。他認為,教育必須解決一個人素質的核心問題,即人文精神。沒有人文精神的教育,是殘缺的、無靈魂的教育。任何知識如果只有專業目標,沒有人類高尚的追求目標和文明準則,非但不能造福社會,往往還會助紂為虐,化為災難。反過來,自覺而良好的人文精神的教育,則可以促使一個人心清目遠、承擔責任、心靈充實、情感豐富而健康。 “教育要想更多的辦法,讓孩子從小就有文化的情感和情懷,這是建設文化強國、教育強國的根本。下一代的內心自信了、強大了,國家才能自信、強大。”
他想為學生點亮人文精神的那盞燈,照亮他們前進的路。
因此,他提出學院的博物館化。
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主要由教研部和博物館部組成,二者分別承擔文化的研究教育和文化的保存功能,相輔相成密不可分。
教研內容包括現當代文學研究、文化遺產研究、民間美術研究、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口述史研究等。教研部內設有三個國字號的文化研究中心,分別為中國木版年畫研究中心、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傳承人口述史研究所。這三個中心既是全國性專案的研究機構,也是研究生們進行學習和實踐的學術基地。自2002年以來已有近30名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在這裡學習、工作並完成學業。
藏品豐富且多姿的博物館是研究院的一大特色。目前,大樓內外陳放了數千件文化珍存,諸多藏品為罕世珍品。此外,研究院也建立了眾多的博物館,包括年畫剪紙廳、雕塑廳、民間畫工廳、花樣生活廳、藍印花佈廳、木活字廳和百花廳等;大樹畫館陳列了馮驥才幾十年來在繪畫、文學文化遺產搶救的成果;大樹書屋為研究院的圖書館,藏書22類凡10萬冊,皆來自他的個人積累;精緻高雅的北洋美術館是舉辦各種藝術與文化展覽的場所。
之所以選擇在一所以理工見長的大學裡建一所人文藝術學院,是因為馮驥才看中了理工大學的「實驗室」制度。在平時的教學過程中,他會採取實驗室的辦法,把某個專案放在一個空間裡,讓老師和學生共同去研究它,一起去作考察。學生也會在這過程中找到感興趣的點,最後慢慢走到學術研究的中心。
把問題放在更廣闊的視野去看,會獲得不一樣的感受。因此,他對學生的期望是「摯愛真善美,關切天地人」。他希望大學生尤其是理工科學生,要在大學期間把視野打開,擁有更寬廣的視野。
2001年研究院剛成立時,馮驥就立下了約定:要在這馳名中外的理工科大學的腹地,開闢出一塊純淨的人文綠地。經過十多年的傾心努力,他兌現了當初的承諾。
「文化疼痛了,你要先痛」
大多數人腦海中的馮驥才,是一位著名作家。 《挑山工》《泥人張》《維也納生活圓舞曲》……這些入選中小學語文課本的優秀篇章伴隨著幾代人的成長。
而許多人不知道的是,近些年,馮驥才將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民間文化遺產保存工作當中。民間口傳文學的蒐集與整理、古城區的歷史資料留存、中國古村落的保護……為了留下這些寶貝,他去各地進行田野調查;為了得到支持,他多次與政府部門溝通;為了籌集保護工作所需資金,他拍賣心愛的畫作。縱然遇到諸多阻礙與坎坷,他依然矢志不渝、癡心不改。
90年代初,馮驥才兩度對文化遺產無意識的保護,是促使他投身文化遺產搶救工作的重要原因──一次是保護江南古鎮週莊的迷樓不被拆掉,一次是捐資修繕寧波的賀知章祠堂。自那以後,他找到了一個進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方式,那就是賣畫。
1994年的某一天,馮驥才從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天津要進行舊城改造。天津城有600年的歷史,舊城區的文物非常密集。舊城改造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但當時開發商的規劃是將舊城區剷平,建造一個「龍城」。這樣一來,老城區裡很多珍貴的東西都將不復存在。
馮驥才急了。身為當時的天津文聯主席,他找到攝影家協會主席說:「咱們組織一個純民間活動,請攝影家採風,我掏錢。」錢從哪裡來?他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賣字賣畫,這是從週莊和寧波留下的「老法子」。
歷時兩年多,攝影師們將整個天津老城區裡外外考察了一番,留下了大量珍貴的圖片資料,編成大型畫集《舊城遺韻》。而馮驥才則整天忙著畫畫、寫字,再將書畫作品拍賣出去──所有的活動經費全部由他個人承擔。
在舊城區開拆之前,馮驥才找到當時的天津市副市長王德惠,建議保留一棟房子蓋一座老城博物館,由他來號召老百姓捐東西。家具、生活物品、照片、資料、書信文獻等,都可以捐款。 「只要老百姓捐了東西,就會惦記這裡,他的感情跟老城就不會分開。」他的建議得到了王德惠的支持。短短幾個月內,博物館就收了幾千件老百姓捐的東西,老城博物館就這樣蓋好了。如今,這座博物館依然佇立在老城的十字街上,向世人訴說著天津老城600年的悠悠歷史。
「投身民間文化遺產的保護,我覺得我是被時代逼迫的,當然也是由衷的。我認為這是命運。到2000年的時候,我和文化遺產保護已經融為一體,就是說從情感上、使命上,我已經把這件事情當作天職去做,不知不覺地反而把小說創作放下了。
從一開始的自發性行動,到後來的主動投入,馮騸才覺得離不開他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立場。作家的立場,不僅是一個思想的立場,而且還帶著一份濃厚的情感。 「身為作家,僅僅把文化當作關切對像是不夠的,你所要關切的文化是人的文化,你所關切的是人,是人對城市的一種自豪、人的一種最珍貴的歷史記憶、人的一種鄉土的情感。
要將民間文化「一網打盡」
2001年,中國文聯找到馮驥才,讓他擔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對民間文化情有獨鍾的馮驥才答應了,並決定到各省去看看,深入了解多姿多彩的民間文化:木版年畫、剪紙、皮影、民間戲劇、民間文學、民間的手工藝和作坊。
但下去一看他才知道,很多民間文化在現代化衝擊下正處於全面瀕危的狀態,可謂風雨飄搖:他從小就知道河北保定白溝的玩具特別好,可到了白溝一問,當地人基本上沒聽過,只知道賣皮包。在鄭州的商代古城,古城土牆上到處都是小販在擺攤賣東西。
他情不自禁想做一件事,這件事比搶救天津老城重要得多。他提出,要對960萬平方公里56個民族的一切民間文化作一個地毯式的調查,並提出一個概念,叫「一網打盡」。
2002年,透過兩會上的提案,他倡議並啟動了「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從此,馮驥走上了民間文化遺產搶救之路。
在山西大同,他多次實地考察當地的雕塑及造像藝術;在閩西土樓前,他跟當地人聊天蒐集土樓資料;在揚州剪紙博物館,他記錄當地剪紙花樣和技藝;在江南周莊,他調查活態的紙馬鋪;在浙東鄉村,他見到了從未見過的福字磚;他還在各地進行演講,喚醒民眾的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和文化自豪感。
在河南的文化普查中,他發現了一個古老的畫鄉-滑縣。入村這天正趕上冷雨澆頭,一行人吃盡了苦頭,但還是深一腳淺一腳地進去了。經過數月努力,他將滑縣年畫獨特的歷史、文化、技巧與習俗寫進了《豫北古畫鄉發現記》。
在湘中花瑤的村莊有位老村長,上世紀大煉鋼鐵時曾保護了寨中上百株參天古樹,被人稱作「古樹保護神」。馮驥才對老人說:“我給您點煙,您是我師傅。”
進行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作,沒有經費怎麼辦?馮驥才還是老辦法,成立基金會,賣自己的畫。
在蘇州的那場義賣,很多朋友都來支持,畫很快就賣光了。馮驥才問賣了多少錢,他們說300多萬元。他說,“好,我現場捐獻”,就在大廳裡把這筆錢全部捐出。
拍賣結束後,人群散去,他對攝影師說:「我在屋子中間站著,你給我照一張相,我跟我的畫合張影。」「這些畫都是我的心血,我喜歡我的畫,都不知道我把這些畫賣了是一種什麼感受。
在民間文化搶救過程中,馮驥才提出了「把書桌搬到田野」的主張,並寫了三篇文章《到民間去! 》《思想與行動》和《文化責任感》,表達了他們這代文化人的學術觀。
有理想的人永遠年輕
自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一開始,古村落便是工作重點。這些年來,由於城鎮化腳步加快,古村落消失加劇,情況危急。
2002年起,馮驥才帶領團隊走遍大江南北尋訪各地古村落,河北、山西、四川、廣西、湖南、江西、安徽……每到一處,他都走村串鄉,記載、調研,尋求保護的途徑。
他發起召開多次會議、論壇,為古村落保護工作鼓與呼。 「中國古村落保護」西塘國際高峰論壇為古村落保護發出了強音,中國傳統村落高峰論壇凝聚眾人智慧探討古村落何去何從,2016年的慈溪會議為「古村落十大雷同」亮起紅燈… …
他還在各種場合強力發聲,讓弱勢的文化發出震耳的強音。在東南大學演講時,年輕學子們對保護古村落這一主題興趣之大,令他非常振奮。
在馮驥才的奔走與呼籲下,多個國家部會聯合啟動了「留住鄉愁-中國傳統村落立檔調查」項目,也組織了「傳統村落保護發展訓練班」。一座座古村落得到發現與保護,在歷經歲月洗禮後重新煥發出盎然生機。
這些年,馮驥又有了新的擔憂。
有些古村落剛被搶救下來,新一輪的破壞就來了。村子有了旅遊價值、品牌價值,政府就把村子買下,把民宅裝潢起來做景點,開闢商業街。馮驥才說:“原住民的文化自覺、村鎮管理者的文化自覺,完全都沒有,人們的眼裡只有利益。這是價值觀的問題,是需要文化自覺來改變的。”
在他看來,知識分子先要自覺,這是文化人的天職;然後要把它喊出來,使之逐漸成為一個國家的自覺;最後,要形成一個地方的自覺,這樣才能把文化遺產保護貫徹下去。
馮驥才先生已經76歲了,但在與他交談的過程中,你會發現他的身體裡住著一個年輕的靈魂。
他對他所熱愛的一切事物都懷有高遠的理想,充滿著不竭的熱情,甚至有著一種堂吉訶德式的孤勇。他將自己奮鬥的四個領域——文學、繪畫、文化遺產保護、教育稱為“四駕馬車”,作為“駕車人”,他每件事都傾盡全力。
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些年來他一直筆耕不輟學,因為在他看來,作家的名字是留在自己的作品裡的。與早年不同,他從純文學創作漸漸投身於非虛構創作,從獲得《小說月報》百花獎的《一百個人的十年》開始,他相繼創作了《搶救老街》《地獄一步到天堂》《泰山挑山工紀事》等非虛構文學作品,著重於民間文化,聚焦小人物的命運。近些年他更是達到了新的創作高峰,出版了個人口述史系列的《無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旋渦》。這四本書可以說是他五十年精神的歷史。
2018年,馮驥才的《俗世奇人》(足本)榮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此前他曾經先後四次獲得該獎。他笑言,文學獎其實是屬於年輕人的,他這個年紀獲獎,一方面對他是一種鼓勵和安慰,讓他覺得“這老頭還行,還能接著寫”,另一方面感覺跟讀者的距離一下子就拉近了。
一首英文小詩裡寫道:「有理想的人永遠年輕。沒有理想的人即使年輕,他的靈魂也爬滿了皺紋。」馮驥才用自己的思考與行動,深刻詮釋了「有理想的人永遠年輕」這句話的真諦。
76歲的馮驥才,依然有理想,依然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