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國人的印像中,莊子是一個消極避世,一個空談玄想的人。這其實是對莊子的誤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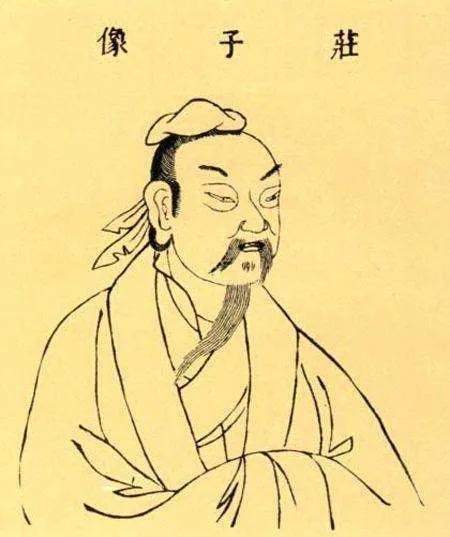
現存的《莊子》有三十三篇,從理論上詮釋莊子社會行為的合理性。莊子闡述的重心,並不是諸如宇宙觀、自然觀、知識論、方法論的純粹意義上的哲學命題,而是人如何在一個充滿危險和傷害的亂世中做到「保身」、「養生」、「盡年”的實踐和經驗問題。其根本點,就是「重生」、「貴己」。莊子所倡導的「無為」恰恰是為了有為和大為,在他無拘無束與看似不經意的文字中,到處充滿人文關懷。
莊子最大的的智慧,就是重生。在莊子的眼中,生命的價值才是無與倫比的。 首先要珍重自己的生命。在面臨世俗名利的時候,莊子強烈主張以生命為本,反對讓世俗名利牽累和禍害生命。在《莊子》一書中,許由、子州支伯、善卷、石戶之農等形象,都不願為了擁有世人看得最重的天下而損害自己的生命。 “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的“不材之木”曲轅櫟樹,為了保全生命,不懈地追求無所可用的境界,最終得所願。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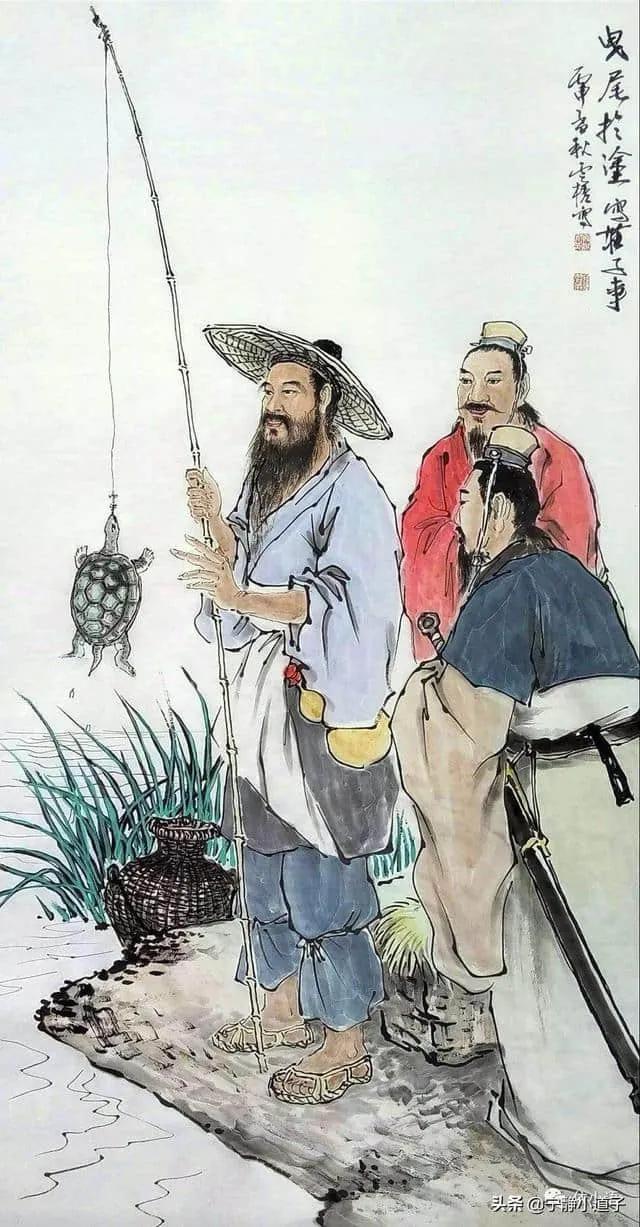
這則記載在《莊子·秋水》的故事所體現出來的,就是莊子對自己生命的珍重。
其次要珍重他人的生命。重生不僅意味著一系列以自我生命為中心的選擇,也意味著深切關懷他人的生命。大王古公亶父在狄人的侵擾下,不忍心為了地盤而使百姓喪命,便依然從鄔出走到岐山之下。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卻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望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者! ——《莊子讓王》
大王亶父的愛,超越了一般人很多很多。他愛自己,愛自己的人民,甚至愛要佔據自己國家土地的人,惟獨不愛自己的地位與利益。
在莊子看來,生命對人生抉擇有決定性的意義,這和孔子、孟子拿仁、義跟生命對比,以一種極端的形式來彰顯仁、義的價值並不矛盾,莊子的重生,主要是反對世人以利傷身累形。
從更深刻的意義上說,重生意味著不能使生命淪落為工具。卡夫卡的《變形記》使人掩卷難忘,格里高爾的遭遇也叫我們思考人的異化。其實莊子很早就反對人的異化:物物而不物於物。想想在現實生活中,人被異化的危險無處不在。物質、技術、權力及其相關的慾求都可以把人異化。莊子的智慧,對現實人生極有警示意義。
除了反對人的異化,莊子還反對把他人工具化。 《莊子·人世間》的櫟社樹的寓言並不是要討論木匠或樹木的問題,而是傳達對現實人生的思考。匠石和櫟樹是兩種價值取向的代表。匠石認為櫟樹是無所可用的'散木”,他的價值取捨的標準是樹木能否滿足做船、做棺材、做器具、做門戶、做柱子等一切世俗功利要求。從他的立場上說,樹木的價值就體現為充當某種工具或手段。他拒絕跟不符合這種價值取向的對象建立有意義的聯繫,所以,面對高大無比、觀者如市的樹,他“不肯觀”“行不輟”,並斥責了對櫟樹嘆為觀止的弟子。跟匠石截然相反,櫟樹把“無所可用”當成“大用”,不懈迫求,一方面堅決拒絕充當工具性價值的載體,一方面堅決反對匠石把自己當做工具。櫟樹用託夢的形式說:“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 ”這句話裡的潛台詞是,我跟你鬱是天然平等的“造化之一物”,不要期求對方成為滿足自己需要的工具性的物。莊子提出的不要讓生命淪落為工具的思想,蘊含著對當時社會的沉痛感悟,也大大張揚了生命的價值和尊嚴,休現了對人的大關懷。
莊子的智慧還體現在他的精神境界。 這是矛盾的兩個方面不斷衝突的內心世界。 一方面,他對人類充滿憐憫,最多情,最溫柔寬仁。另一方面,對污濁黑暗的世界,冷眼看穿,冷酷犀利。莊子在污濁的人世間保持著清潔的精神,他超凡絕俗,拒絕誘惑,把自由的價值看得至高無上,不屑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莊子反對戰爭,反對暴君暴政,抨擊統治者殺戮百姓的罪惡,主張無為政治,奉勸君主們少做點壞事,呼籲人們遠離充滿危險和傷害的社會環境。 在《莊子·養生主》中,莊子用“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訴人們:一個人如何在充滿危險和災難的亂世中保全性命,關鍵在見識、智慧。
讀莊子的文章,我們真是進入了一個奇幻的世界。 《逍遙遊》中,鯪、鵬、蟬、學鳩、斥鷃、朝苗、蟪蛄、冥靈、大椿、彭祖……林林總總,千差萬別,莊子反覆對比,比如用鯤鵬和蟬、學鴞、斥鷃做對比,用適郊野者、適百里者和適千里者做對比,用小年和大年做對比,用「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跟定乎內外之分的宋榮子、禦風而行的列禦寇做對比等,最終引出他心日中的人生最高境界,這就是至人、神人或聖人。這似乎是超越現實、超越自然的虛幻的人生自由,莊子其實是用一系列的實物啟發我們:人生在世,應當有宏大的志向,高遠的追求。
每一個人都應該不斷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莊子·秋水》中,莊子宣揚人類精神的一種理想境界,即一種不受地域格局,不受時間拘囿,並且不被所受教育束縛的大境界。要消除河伯和坎井之蛙那種畫地為牢、固步自封、安於小我的心態。即便我們已經有了較高的精神境界,也不能夠自滿。北海之大,吸納萬川,春秋不變,水旱不知,然而海神未嘗自我讚許,反而深刻地認識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自己在渺渺宇宙中“方存乎見少”。這種蘊蓄博大而不自滿的精神給我們以啟迪。
還記得《莊子外物》篇中的那個任公子嗎?他用大鉤、巨緹和五十頭牛做成的釣餌,釣上來一條驚天動地的大魚。你不得不佩服莊子的想像力,藉這超絕人寰的形象,他告訴我們:人要有大想法、學說、大抱負、大作為。而作為統治者,如果違背人民的性命之理瞎折騰,即便出自善意,也一定會導致悲慘的結局。不是嗎?倐和忽為了報答渾麋,給渾姦日鑿一竅,最終卻導致渾完整死亡。

“無路可走,卒歸於有路可走。”這是劉熙載概括出的《莊子》和莊子的意旨,也是莊子的大智慧。善於逆向思維,往往能從一般人看不出價值的地方發現價值,是莊子獨特的睿智。曲轅櫟樹做舟則沉,做棺槨則速腐,做器則速毀,做門戶則液樠,做柱則蠹,被匠石指責為無用的散木。莊子卻揭示出,“無用”正是櫟樹的“大用”,它沒有像楂梨橘柚蓏之屬那樣,因此成長得頂天立地,得以終其天年。由“無用”到“大用”,體現出的是莊子不同凡響的思維取向和視野。
莊子常常從人生的絕境中發掘出光明的前景,指出一條實現突圍的路徑。衛國的哀駘它醜得使天下人驚駭。這是人生的一種絕境,哀駘它卻極大地發展了自己的內在潛能,使精神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面對世人認為無可奈何的死與生、存與亡、困厄和通達、貧窮和富有、有才德和無才德、毀謗和讚譽、飢和渴、寒和暑等一切變化,他的內心不為所動,平和、快樂、通暢而不失於愉悅,充滿盎然的生機。他高超的德行就在於養成了這種外在事物無法搖蕩的內心的純和。而正是由於他的德行大大超越了常人,人們忘記了他形體的殘缺和醜陋,感受到一種異乎尋常的巨大魅力。跟哀駘它相似,子輿、子來都面臨著某種困境。子輿大病一場.變排腰彎背弓,五臟比頭都高,下巴藏到肚臍眼,肩膀高過了頭頂,彎曲的頸椎骨指向天空。然而他安然處之,世俗的哀樂不能驚擾他內心的平靜。子來有了病,氣喘吁籲地將要死亡。可是他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變成鼠肝也好,變成蟲臂也罷,無往而不可。這種奇特的思想,顯示了莊子對社會人生的大同情和大關懷。他試圖使世人在陷入絕境的時候,靠內在精神力量的培育自解倒懸之苦,實現人生的突圍。外國的海倫·凱勒、奧斯特夫斯基、典子,我國的司馬遷、皇甫謐、張海迪等,都是實踐了莊子的這種精神的。
鮑鵬山說:“在一個文化屈從權勢的的傳統中,莊子是一棵孤獨的樹,是一棵孤獨地在深夜裡看守心靈月亮的樹。”
劉夢溪說:“莊子所追求的這種個體生命的自由,見諸生活,是一種享受;見諸人生,則是一種審美。”
他們都是深刻理解莊子智慧和價值的人。
在這個充滿物慾與迷惘的時代,莊子的智慧是我們食糧和良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