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學派,是一個完全獨立於國家之外的組織,它不聽從任何國家的指令,不受到任何君主的調遣,每當國與國之間出現了摩擦,墨家就會負責為雙方調解,每當有大國強國,對弱國實施了侵略活動,墨者就會幫助弱小來保家衛國,而且這群人不圖錢財、不圖名位,唯一的目的,就是實現他們學派中那個沒有戰爭,沒有貧富差距的理想社會。我們很多人認為,墨家思想的極致就是兼愛非攻,但實際上,他們要比我們想像中的更為激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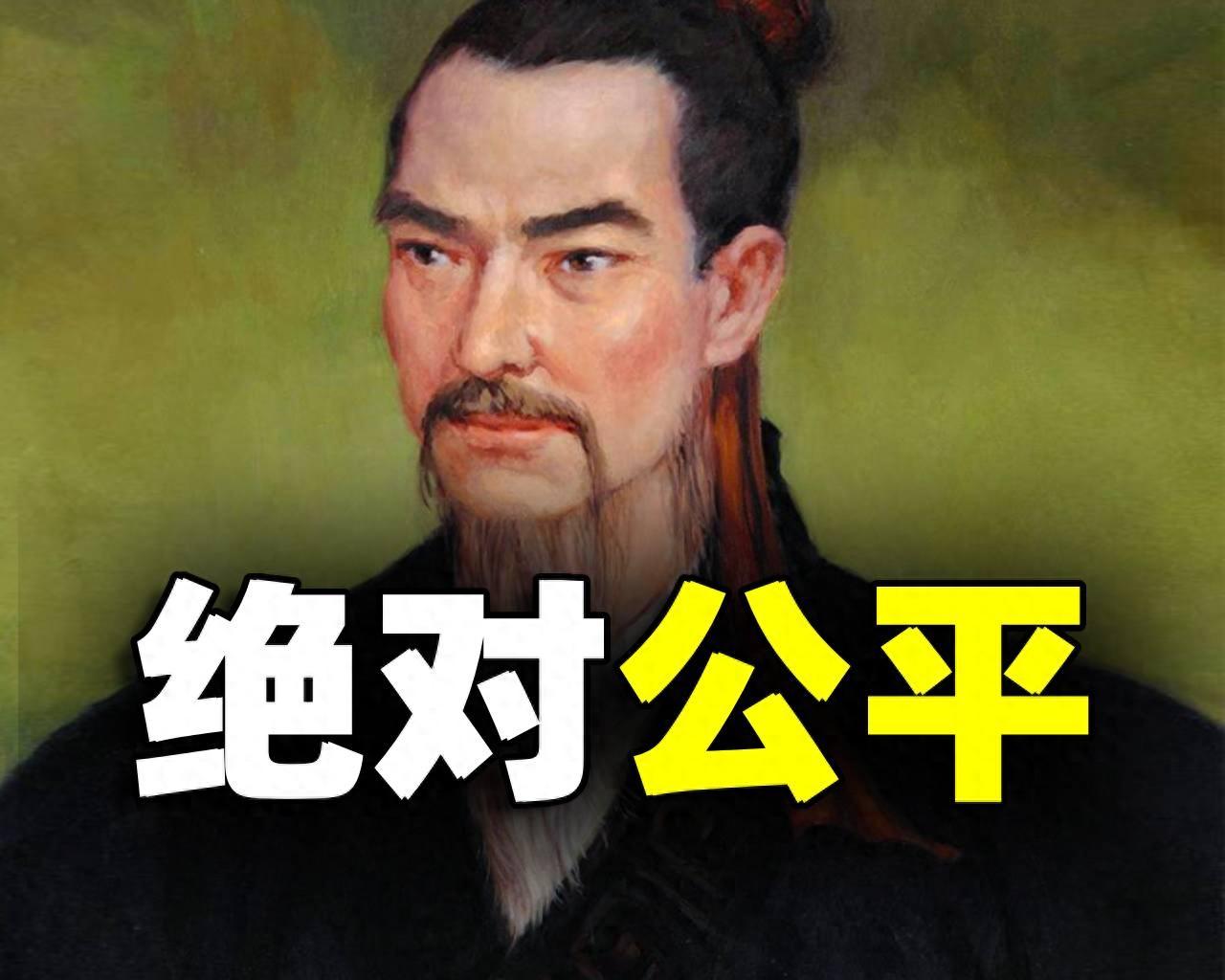
墨家提倡「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意為國與國之間,沒有大小強弱的分別,人與人之間,也沒長幼貴賤的差別,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應該是一種完全平等的關係,甚至是墨家也提出了「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意思就是要透過推舉的方式,來選擇出百姓所認為君主,所認可的官員,這樣百姓才能心甘情願的聽從調動,聽從他們的命令。

墨家對於墨者的管理極為嚴格,要求他們必須節儉、禁止享樂,反對一切的娛樂活動,不能追求任何物質上的享受,墨者要將所有的財產上交墨家,然後像苦行僧一樣,日夜不休的維護天下和平,甚至要隨時準備為此獻出生命,墨者必須要遵守兼愛的原則,也就是做到毫無差別的愛,對待陌生人,就像是對待父母一樣。反過來說,對待父母,就像是對待陌生人一樣,所以孟子將墨家稱為是“禽獸之學”,認為墨家學派,是一門無父無君的反人性的思想,這個時候就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在孟子的滕文公中寫道:“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即歸墨。”也就是說在孟子眼中的,這門反人性的思想,竟然成為了當時社會上的熱門學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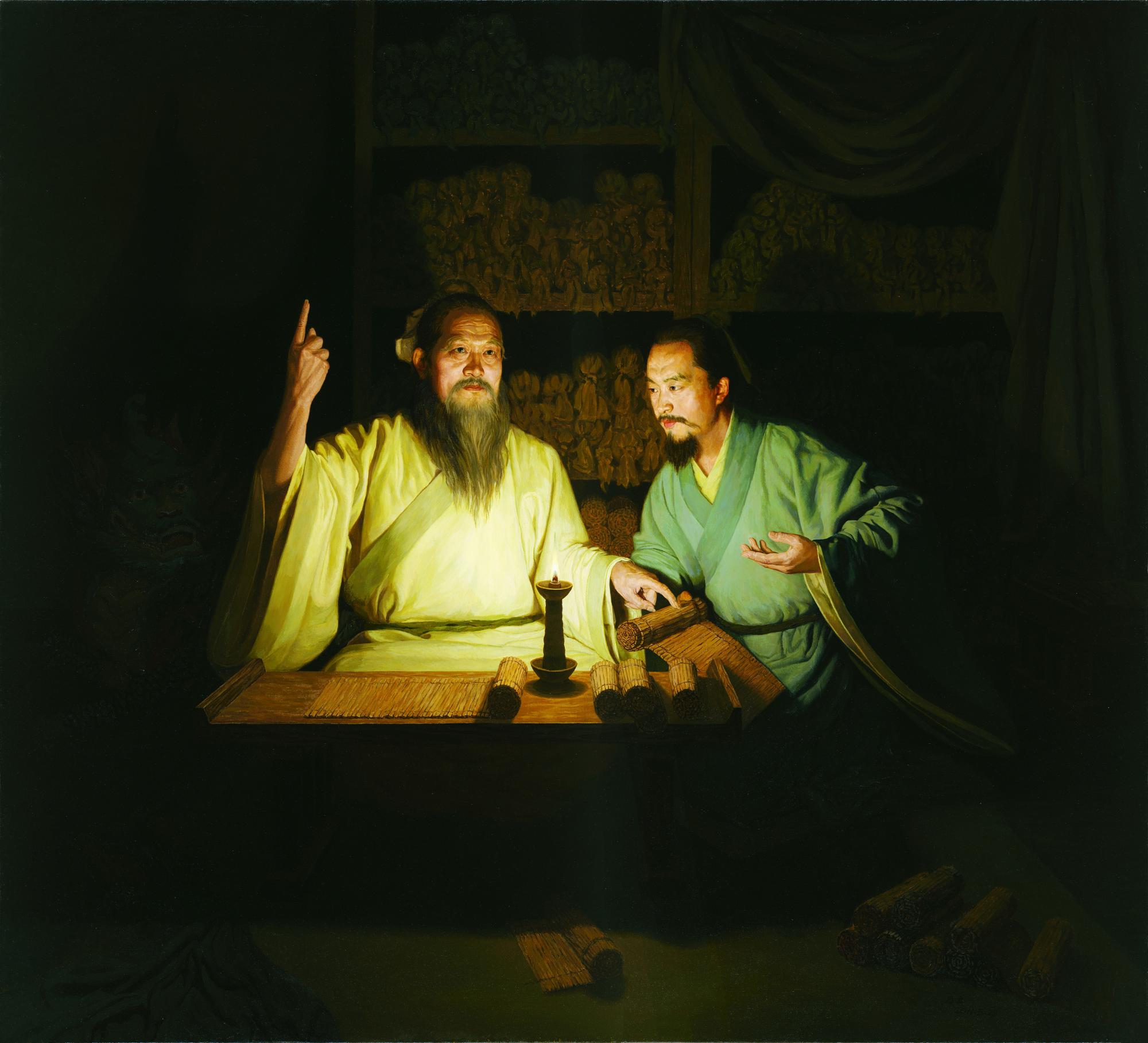
同樣在韓非子的顯學篇中也寫道:“世之顯學,儒、墨也。”也就是說在楊朱學派沒落之後,墨家又開始與儒家共分天下,成為了韓非時期的兩大顯學,換句話說,反人性的墨家學派,竟然淘汰了順應人性的楊朱學派,我們都知道楊朱學派講“貴己”,也就是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命,而墨家學派卻是“賤己”,要求墨者將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顯然對於個人來說,楊朱要比墨家更為現實,那為什麼當時的學者,不加入楊朱學派,反而加入隨時,都有可能丟掉性命的墨家學派呢?墨家到底是如何解釋兼愛的呢?這也就牽扯到了墨家的經典——墨經。
和儒家一樣,墨家也定義了一些倫理學上的概念,比如仁義忠孝行,什麼是仁呢?墨經說仁就是不以愛人為目的的愛人,比如很多君主口中的仁愛,無非是為了讓百姓為他們征戰,這個就是一種目的,什麼是義呢?義就是把利讓給他人,但卻不求取任何的利益,忠不是一味的順從君主,而是去做有利於國家的事,甚至不惜威脅君主的地位,孝也不是一味的順從父母,而是去做有利於父母的事,有時也要去違背父母的意願,行就是真正的有所作為,而不是被慾望左右的行為。

墨家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兼愛”,人為什麼要兼愛?人真的能做到毫無差別的愛嗎?其實兼愛的全名應該是“兼相愛,交相利”,意思就是為什麼一個人要講義氣呢?在墨子看來,單純從道德之上,讓人去講義氣是沒有作用的,只有講義氣能夠帶來利益,人們才會自發的去講義氣,同樣只有愛別人時,別人也能夠愛自己,人們才能夠自發的去愛別人,那如果一個人就只希望別人愛自己,自己就是不去愛別人怎麼辦呢?後面還有一句,叫作「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從這裡就引出了墨經中「殺盜非殺人」的想法。意思就是用刑罰,幫助他學會怎麼去愛人,當然這一條,主要針對的是春秋戰國時,那些「欺壓百姓,暴奪民食」的君主和貴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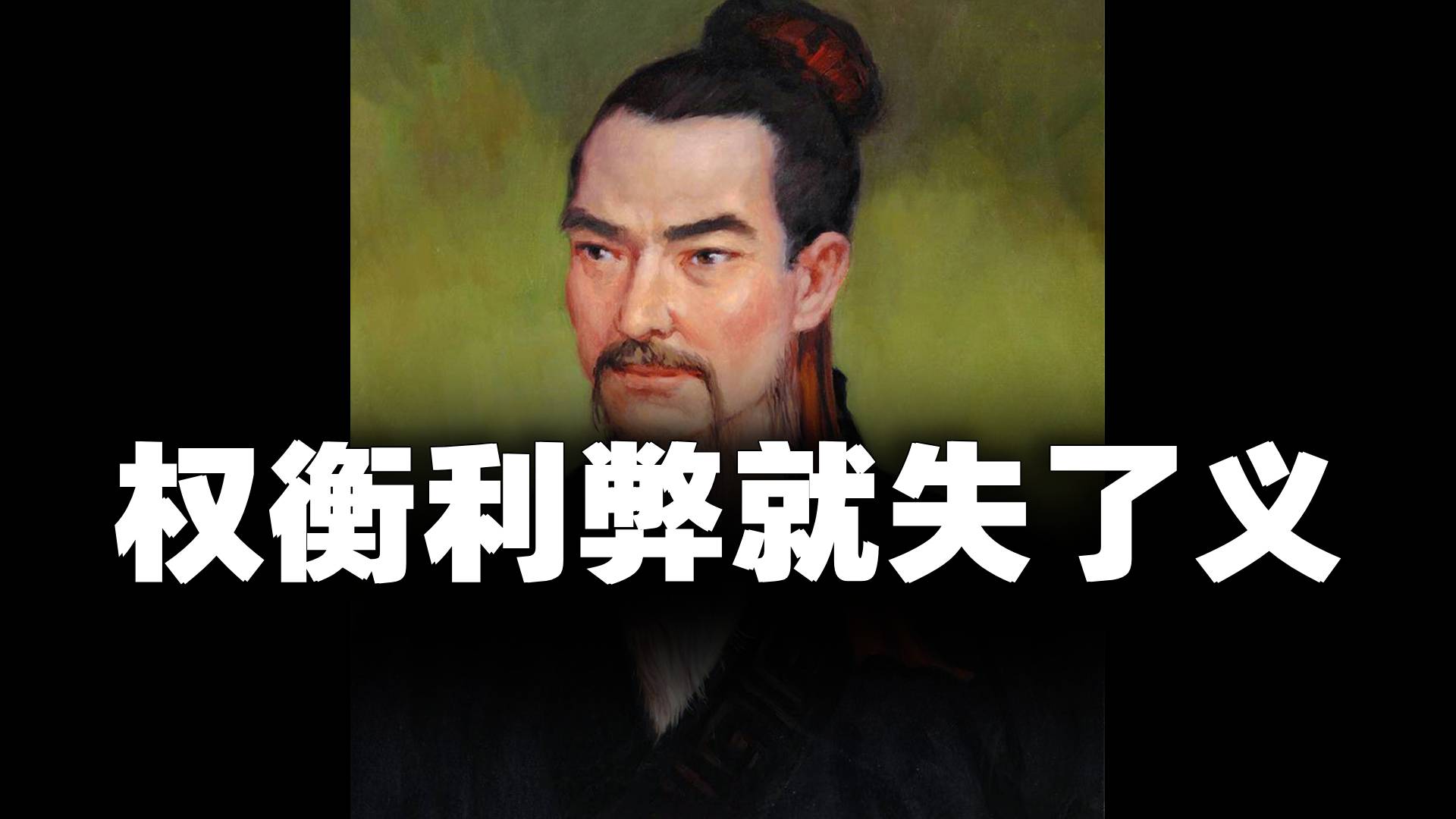
在列子的楊朱篇中,曾記錄了一個叫作一毛不拔的辯論,說是墨家的禽滑釐問楊朱,如果拔掉你身上的一根汗毛,用來拯救全天下的人,這樣的事情你願意幹嗎?楊朱說這個天下的問題,就不是一根汗毛能夠解決掉的,禽滑釐又問,那如果能夠解決掉,你願意去乾嗎?楊朱沒有回答,後來楊朱的弟子孟孫陽,對禽滑釐說,如果損害你的皮膚,然後給你萬兩的黃金你願意乾嗎?禽滑釐說願意,孟孫陽又問,如果砍斷你的肢體給你一個國家,你願意去乾嗎?其實這個就是楊墨兩家的主要分歧,同時也引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個人的生命,和國家,和天下的安危之間,到底哪個比較重要?這就是早期版本的電車難題。
有五個人被綁在一條軌道上,一個人被綁在另一條軌道上,此時一輛失控的電車正疾馳而來,在你的手邊恰好擺著一個拉桿,如果不控制拉桿,電車就要碾壓五個人,如果控制拉桿,電車就要碾壓一個人,那你是選擇犧牲一人拯救五人,還是選擇袖手旁觀,任憑電車去碾壓這五個人呢?在墨經中是這麼解釋的。首先墨子說,在我們所做的事件中,衡量事件輕重的概念叫作“權”,這個權不是對的,也不是錯的,而是正當的,什麼叫正當的呢?砍斷手指來保存手腕,這是在利中選取大的,在害中選取小的,這個就是正當的,這就好像是我們遇上強盜,為了保命只能砍斷手指,這個就是利,而遇上強盜就是害,接下來是重點,叫作“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

殺一個人有利天下,並不是殺一個人能夠有利天下,殺死自己有利天下,這是殺死自己能夠有利天下,什麼意思呢?墨子首先批判了聖母心,犧牲他人來拯救天下,這不是正義的行為,不是真正的有利於天下,你如果有犧牲的精神,犧牲自己來拯救天下,這才是正義的行為,這才是真正的有利於天下,再往下是「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意思就是我們在面對問題時,總是會專注於求,專注於得到什麼,但是這種關注於求的行為,本質上就是在權衡利弊,也就是說當你在考慮,你在想著犧牲誰的時候,就已經脫離了正義的範疇,換句話說,不管你接下來,要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歸根究底都是不正義的行為,你袖手旁觀不正義,你拉動拉桿也不正義。
所以「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義也。」這時候就沒有了利和義的分別,你只能在兩害之中,也就是在犧牲一個人,和犧牲天下人之中,選擇一個害處最小的,這個叫“兩害相權取其輕”,只能追求這種“合義”的行為,當然墨子也一再的說明,非為義也,這不是什麼正義的,值得誇獎的行為。其實看到這裡大家就能明白,在墨家的思想中,除了自然科學方面的探究之外,還存在著大量關於倫理學、社會學、邏輯學方面的論述,所以墨經又被稱為是墨辯,與古希臘邏輯學、古印度因明學,並稱為是“世界三大邏輯學”,如果能夠理解以上部分的話,那我們就再進一步,看一下墨家在邏輯學方面的論述。

首先在墨家的思想中認為,人們有著認識這個世界的能力,叫作“所以知也,而不必知”,人們都有著知的能力,但這種能力不等於知識,那怎樣才能夠獲得知識呢?墨經說「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以其知論物而知之也著。若明。」意思就是將認知的方式,分為了兩個過程,第一個是看到外界事物,然後得到了這個知識,例如我們看到了花,眼睛接受到了花的顏色,和花的形狀的信息,這是一種感性認識的過程,第二個是看到了外界的事物,然後透過推論發現了事物的其他屬性,例如我們進一步思考花的種類,花的生長習性,用已知的邏輯和知識來進行推論,以便於更了解事物的本質,這是一種理性認識的過程。

在知識方面,墨子將知識的來源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我們親身的體驗,例如我們觸摸到火,所以發現了火灼燒的屬性,第二類是透過權威的傳授,例如有些孩童沒有碰過火,但我們告訴他火有灼燒的屬性,第三類是推論的感悟,比如我們透過已知的火的屬性,來推論火,或者是其他事物可能具有的屬性,再往下有些難以理解,墨子將知識拆分成了四個面向。分別是名的知識,實的知識、相合的知識,行為的知識,比如說這裡有匹馬,其中“馬”就是名的知識,我們稱之為“馬”,而馬本身是實的知識,也就是實際存在的事物,我們可以用名稱來代指馬,但是這個馬的名稱,卻無法代表馬的全部。
再比如說我們都睡過床,知道什麼是床,知道床這個名稱,但是這一天我們去到了野外,想要睡覺但沒有了床,怎麼辦呢?我們找來幾張報紙,鋪在草地上,此時報紙就有了床的概念,也就是說我們所認為的床,我們所稱為床的東西,都是對於床這個概念的模仿,但是這種名稱不能夠代表床的實質,同樣馬也是一個名稱,我們可以製造類似馬的事物,但並不能夠模仿出馬的實質,因為名稱是名稱,實在是實在。

除此之外,墨經還將事物的名稱分為了三類,分為是達名、類名、私名,達名指的是普遍的名稱,比如我們說動物,無論貓、狗、鳥、魚都屬於是一種動物,類名範圍要小一些,指的是一類具有共同屬性的事物,比如我們說哺乳動物,這裡就剔除了鳥類和爬行動物,私名則是一個具體的命名,比如說你的姓名,它就特定的指明一個人,而不適用於其他的事物。人們為什麼要進行辯論呢?這麼摳字眼不是一件無意義的事情嗎?因為辯論,可以讓我們明是非、審治亂、明同異、察名實、處利害、決嫌疑,這就像是去醫院看病一樣,醫生在開出藥方之前,必須要經過一系列的檢查,這個檢查其實就是一種辯論,一種查名實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