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州吁籲正要發兵討伐鄭國,忽然想起鄭、齊兩國剛剛簽訂了「石門盟約」。兩國締約,遇事互相援助,衛若伐鄭,齊必相救,兩國打一國,衛國豈是對手?

州吁將自己的想法告訴石厚,石厚獻策說:“周初分封諸侯有五個等級,即公、侯、伯、子、男,異姓國家,現在只有宋國(子姓,初封為殷商後裔微子啟,都邑在今河南商丘)稱公爵為大;同姓國家中,只有魯國(姬姓,初封為成王叔父周公姬旦,都邑在今山東曲阜) 稱叔父為尊。主公如果想討伐鄭國,就必須派使者到這兩個國家去遊說,求其出兵幫助,並和陳國(媯姓,在今河南淮陽縣)、蔡國(姬姓,在今河南上蔡縣)的軍隊結成統一戰線,五國共同伐鄭,何愁不勝?”
州吁籲想了想說:「陳、蔡都是小國,歷來順從周王。如今鄭國和周王之間產生了隔閡,陳、蔡肯定早已聽說了,讓他們幫助攻鄭國,不愁不來。
石厚聽了,笑笑說道:“主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昔日宋宣公傳位於他的弟弟宋穆公,宋穆公死前,想報答哥哥的傳位之恩,沒有把君位傳給自己的兒子公子馮,而是傳給他哥哥的兒子與夷,即宋殤公。宋殤公心地狹窄,公子馮怕被殺害就出奔到了鄭國,想藉用鄭國的力量奪回君位,這一直是宋殤公的一塊心病。我們約宋伐鄭,這豈不正中其心懷?至於魯國,魯隱公只是代理國君,太子軌因年齡小尙未正位。正因為此,魯隱公執政名不正,言不順,軍政大權實際上操縱在公子翬(hui)的手裡。此人貪財好利,只要主公能賄賂以重金,他肯定會出兵助陣。”

州吁籲聽了大喜,立即派遣使者前往魯、陳、蔡三國,唯有使宋人員難挑,石厚舉薦寧翊,說:“此人博古通今,口才伶俐,一定能完成任務。”
州吁就派寧翊使宋。寧翊來到宋國,宋殤公問:“貴國為何要討伐鄭國呢?”
寧翊回答:“鄭伯無道,殺弟囚母,公孫滑逃命到我們衛國,他又不念伯侄之情,率師前來討伐,先君懼怕鄭國強大,只好忍辱謝罪。現在我國新君即位,想洗雪恥辱。衛、宋兩國同仇共恨,所以,特派我前來借兵。”
宋殤公不解,問:“宋國和鄭國並無隔閡,同仇共恨從何談起呢?”
寧翊環顧左右說:「請屏退侍從,我想單獨和您談談。」宋殤公讓侍從全部退下,然後問:「你有什麼話,只管說吧!」寧翊反問道:「您的國君之位是誰傳給您的?”“叔父穆公傳位於我。
“自古以來都是父死子繼,穆公雖有堯、舜之心,怎奈公子馮卻無人臣之意。穆公傳位給您,公子馮為何不甘心在宋輔政呢?分明是對失去君位懷恨在心嘛!現在公子馮雖身在異國,但心裡卻始終可沒有忘記重返宋國啊!鄭國接納了公子馮,他們交情已深,一旦鄭莊公擁馮興師向您問罪,宋國人民又感念穆公之恩,因而懷念他的兒子,內外生變,難道您的君位沒有失掉的危險嗎?所以,我這次前來借兵,名為伐鄭,實際上是替您消除隱患啊!如果君侯能出面主事,衛國願意馬前鞍後效勞,若能滅掉鄭國,宋則除去了隱患,衛則洗雪了恥辱,豈不是兩全其美!”

宋殤公聽了這些言語,果然心動,說:“何不約魯、陳、蔡一同舉事?”
寧翊告訴他:“我國國君已分別派遣使者去了。”
宋殤公聽了大喜,於是答應親自率領宋軍伐鄭。太宰華父督與公子馮關係密切,不願意宋殤公伐鄭,勸阻道:「衛國使臣的話聽不得。如果鄭伯殺弟囚母有罪,州吁籲弒兄篡位能說無罪嗎?望主公三思而後行。
宋殤公聽不進華文督的勸告,命大司馬孔父嘉為將護駕,自領中軍出發。
魯國公子翬接受了州吁的賄賂,便不由隱公作主,自率大軍前來會師。陳、蔡的軍隊也如期到達。宋殤公爵位最高,被推為盟主,衛國石厚為先鋒,州吁自領一支軍隊殿後,五國共有戰車一千三百乘,將士十萬之眾,來到鄭國東門外扎下營寨。
大兵壓境,鄭莊公召來群臣商議,有人主戰,有人主和,意見不一。
鄭莊公笑了笑說:「你們的意見都不是上策。州葉篡權新立,未得民心,所以藉故一些舊的恩怨興兵來伐,其目的不過是想立威以服眾;魯國公子翬貪圖賄賂,事不由君;陳、蔡都與鄭無仇,也沒有必戰的意思;只有宋殤公是真心伐鄭,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標是公子馮,並不是寡人。殤公必移師長葛。交鋒,只許敗,不准勝,白送給州吁一個勝仗,州吁贏得勝利之名,就會得到滿足,他國內尚未安定,那敢在此久留?我聽說衛國大夫石碏忠心耿耿,他對州吁籲大為不滿,衛國不久就會發生政變。所以,別看現在大兵壓境,其實有驚無
險。 」

眾大臣對莊公的一番話將信將疑,鄭莊公命瑕叔盈率一支軍隊護送公子馮去長葛。然後又派人給宋殤公送去一封信,信上說:「公子馮逃到我們鄭國,因是貴國穆公後裔,我不忍心加害於他。現在,我讓他到長葛去伏罪,宋公可以自己去處理此事。
宋殤公見信,果然不告而別,率領自己的人馬包圍長葛去了。魯、陳、蔡三國見宋兵移動,也都產生了撤兵的念頭。就在這時,忽報公子呂率鄭軍從城中殺出,魯、陳、蔡都不願意向前,只在原地袖手旁觀。石厚只好引兵與公子呂交鋒,戰沒幾個回合,公子呂敗下陣來,倒拖方天畫戟而走。石厚追到城下,守城士卒早已放下吊橋將公子呂接入城中。石厚打了勝仗,命令士兵將新鄭城外莊稼收割殆盡,用來犒勞各國將士,然後下令撤兵。眾將士不知石厚意圖,齊來秉告州吁籲說:“我們的軍隊銳氣方盛,正好乘勝追擊,怎麼先鋒官卻要下令班師?”
州吁一時也弄不明白,派人召來石厚詢問。石厚說:「請主屏退左右,臣有密事啟奏。
州吁籲身邊人都退去。石厚說:「鄭國國富民強,鄭伯又是當朝卿士,現在被我軍打敗,這便足夠建立主公的威信。主公新立,國事不穩,我擔心國內出事,如果在此長久滯留,有了內亂又如何應付? 」州吁籲醒悟,說:“多虧愛卿提醒,都怪我考慮不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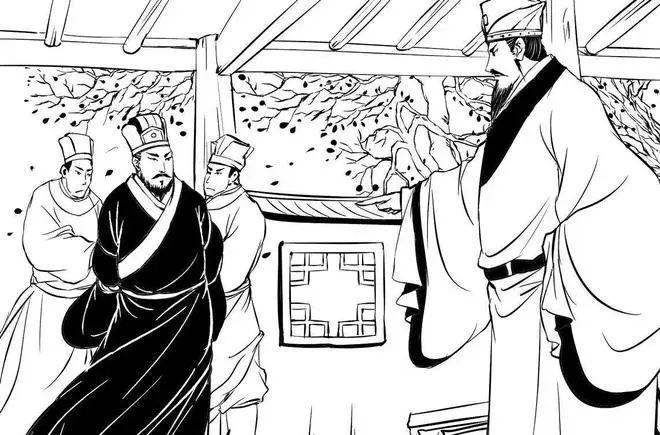
正說著,魯、陳、蔡三國主帥都來祝賀胜利,也都要趁機班師。 這正合州吁、石厚心意,於是盡班師而去,這次戰役總共圍困鄭國東門五天而已,歷史上就叫“東門之役”。
班師路上,石厚自恃有功,命令三軍將士沿途高奏凱歌,給州吁籲。州吁籲宇軒昂地回到本國,哪知聽到路邊看熱鬧的人卻唱出一首不中聽的歌謠,歌詞是:
一雄斃,
一雄興,
歌舞變刀兵。
何時見太平?
恨無人兮訴洛京!
州吁聽了,很不高興,他問石厚:“我們已經打了勝仗,怎麼還得不到民眾的擁護呢?”
石厚回答:“臣父石碏為前朝上卿,國人都信服他,主公若能將他召人朝中輔政,便會國泰民安。”

州吁籲回到都城,派人持白璧一雙,稻米五百鐘,去請石碏人朝議事。哪知石碏藉口疾病在身,堅辭不受。
州吁又向石厚:“你父親不肯入朝,寡人屈身到府上去問計合適嗎?”
石厚怕父親閉門不見,讓州吁籲下不來台,就說:“我代替主公跑一趟吧!”
石厚回到家中,對父親說:“新君主對您十分敬重,讓我來替他召你入朝。”
“召我幹什麼?”
「只為國中人心不穩,害怕君位不能鞏固,想求父親獻一良策。」「諸侯即位,都要先派大臣到週天子那裡去請求'冊命',有了周王的'冊命'和賞賜的冕冠車服,國人自然就信服了,何愁國事不穩?”
石厚聽了很高興,說:“父親的主意很好,只是無緣無故去朝拜周王,周王肯定會起疑心,如果有人能先在周王那裡幫助疏通一下就好辦了,請父親說說,派誰去最合適。”

石碏假裝想來想去,過了一會兒說:“陳桓公忠順周王,朝拜殷勤,很得周王歡心。衛國和陳國一向和睦,最近又有借兵相助之誼,若新主能親自前往朝拜,央求他在周王面前美言一番,然後入周去請冊命',肯定能成功。”
石厚回到宮中,將父親的話對州吁複述一遍,州吁籲喜不自禁,緊命人備了一份厚禮,命石厚護駕,便要親自去朝拜陳侯。石厚剛走,石碏咬破食指,寫一血書,要陳桓公務必幫衛國除害,將州吁籲、石厚殺掉。
州吁和石厚來到陳國,陳侯派公子佗出城迎接,先安置在客館裡,公子佗告訴他倆:“陳侯已經做好了準備,明天在太廟裡會見你們君臣二位。”州籲見陳侯招待殷勤,心中不勝高興。
第二天,石厚先到,見太廟門口豎著一板白色木牌,上寫"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者,不准進入太廟”,石厚問公子佗:“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我國先君的一句遺訓,我們國君不敢忘記,立此以教子孫。”
石厚不再懷疑,接著州吁也趕來了。二人走進太廟。公子佗先緊走幾步,來到陳侯身邊站定,然後大喝一聲:“奉週天子之命,只拿下弒君姦賊州吁、石厚二人,其餘俱免!”

石厚聞言,還想拔劍搏鬥。此時,埋伏在太廟裡的武士一擁而上,早將二人擒住,哪裡還能動彈?然後,公子佗又宣讀了石碏的血書,大家才知道州吁和石厚被擒,原來是石碏的主謀。
陳侯與石碏交情深厚,他知道石厚是石碏的親生兒子,不忍心殺他,派人到衛國去請示石碏。衛國文武大臣也都說:“篡逆弒君,州吁是首惡,石厚是協從,應當只殺州吁,石厚可以從輕處理。”
石碏不許,說:“州吁之惡,都由逆子釀成,你們替他求情,莫非懷疑我有舐犢私心嗎?”
於是,石碏要親自到衛國去監斬石厚,卻被家臣糯羊肩勸住。最後,由猛羊肩代替主子去監斬了石厚。石碏為了安定國家,不惜殺掉自己的親生兒子,當時人們稱讚石碏這一舉動是大義滅親,「大義滅親」這一成語就是出自這個故事。
衛國除掉州吁之後,從邢國(今河北邢台)迎回了公子晉當了國君,史稱衛宣公。衛宣公以石碏為國老,從此陳、衛兩國更加鬱睦親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