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代的人稱他為藝術怪獸
人類的慾望 掙扎與痛苦
在他的作品中放大
表現了人類激情的形式
他將雕塑藝術推向了現代社會
他的一生交織著醜聞與榮耀
他是偉大的藝術家
他也是《偉大的思想者-羅丹》

巴黎的羅丹博物館,是藝術愛好者的朝聖之地。很多人都以為這座博物館是由羅丹的故居改建的,其實這是個誤會,羅丹故居也是博物館的一部分,但它的位置並不在這裡,而是在巴黎郊區一個叫默東的小鎮。

十月一個清冷的早晨,我們趨車半小時來到默東。進入故居庭院的正門,其實在這兩排看起來很有氣勢的栗子樹的那一邊,但為了不破壞落葉的景緻,管理員帶我們從側門進入。隔著灌木籬笆的這座紅磚巨石、屋頂高聳的路易十三式鄉間別墅,就是羅丹的故居,他生前的大部分時間都工作和生活在這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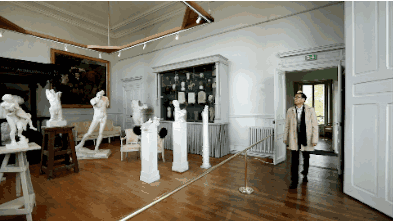
2017年是羅丹逝世100週年,羅丹故居中的陳設基本上還保持著一百多年前的樣子,與羅丹的盛名相比,他的故居陳設顯得太過樸素。餐桌上,雕塑與餐具隨意地擺在一起,據說羅丹喜歡把自己的作品放在餐桌上,一邊吃飯,一邊欣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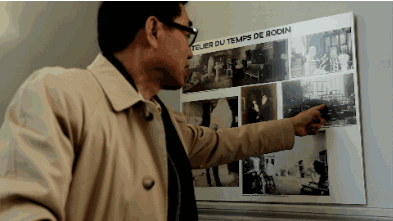
老照片拉近了歷史與現實的距離,終於讓我們有了實實在在的感覺,羅丹曾經在這樣一個空間中存在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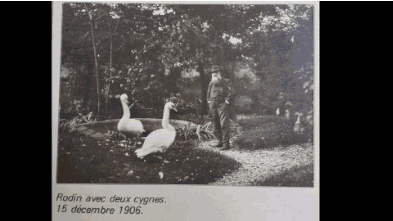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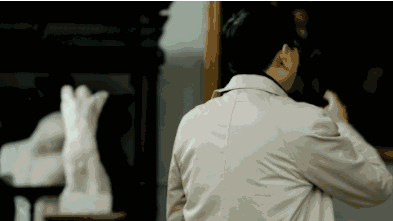
王魯湘:羅丹這個大客廳改造成一個工作室以後,空間還是不夠,他又把外面這樣一個大陽台改造成了一個陽光房,在這個地方陽光明媚,他可以在這個地方工作,你看這裡還有兩個羅丹當年用過的做雕塑的小台子,他在這個上頭可以一邊看著他的美麗的花園,一邊在這個地方做著他的小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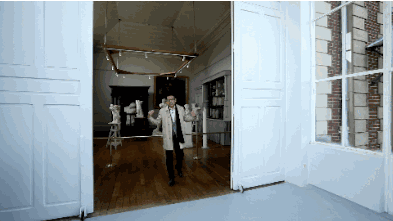
羅丹是最早被介紹到中國的西方現代藝術家,那是在一個世紀前,在五四運動後的1920年,《新青年》上刊登了羅丹的四幅作品:《羅丹自畫像》、《青銅時代》、 《思想者》和《吻》,並且有專門的文章介紹了羅丹作品的反傳統精神。在之後的大半世紀裡,一直有先進知識分子不斷地將羅丹的作品和他的藝術價值介紹到中國,其中包括美學大家宗白華和文豪魯迅。魯迅曾經遺憾地說過,“羅丹的雕刻,雖曾震動了一時,但在中國卻並不發生什麼關係地過去了。”

歷史後來的進程,或許可以告慰魯迅先生的遺憾。 1993年,《法國羅丹藝術大展》在中國美術館舉行,包括《思想者》、《地獄之門》在內的113件原作來華展出,在一個月的展出時間裡,觀眾超過十萬人,在那個年代,可以說是盛況空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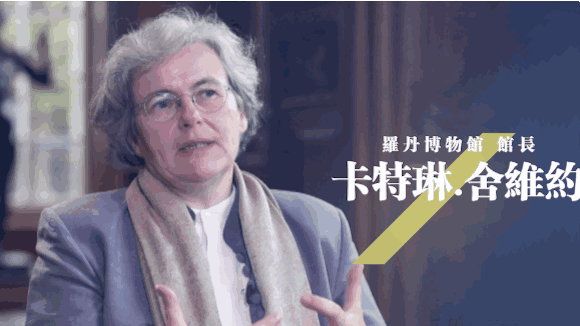
王魯湘:就我的理解,就是世紀之交的羅丹,之所以在中國產生這麼大的影響,超過了其他很多,其實也非常有名的雕塑家,可能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正好中國處在一個社會和歷史的轉型的時候,我們很多的人,就把羅丹理解成為了一個人文主義者,一個啟蒙主義者。
卡特琳‧舍維約:確實中國正在經歷非常大的變化,我們能夠很明顯地感覺到,中國和西方都在渴望著文化的交流,特別是在西方,我們一直對中國充滿著好奇、幻想,特別是法國人。羅丹很適合中國人重新發現自己的文化,因為羅丹這個藝術家會不斷使用很有流動感、不斷變化的藝術表達形式,這是羅丹美學的一個特徵。所以我認為這是為什麼羅丹的藝術呼應了當代中國文化狀態的原因。

故居工作室的窗外正對著羅丹的墓地,1917年羅丹和夫人羅絲被合葬在這座《思想者》雕塑的下面。在這段珍貴的歷史影像中,可以看到當年的葬禮非常隆重。 《思想者》身後,是故居的展示館,擺放的大都是羅丹作品的石膏原作。這裡可以看到羅丹那些著名作品的不同版本,因為羅丹在創作的不同時期,從小稿到正稿都有著不同的變化。行走其間,好像行走在羅丹雕塑的樹林中,不知不覺就產生了一種親近。

巴爾札克是羅丹推崇的偶像,1891年,羅丹受法國作家協會委託,創作文豪巴爾札克的紀念肖像。他花了數年時間,通讀巴爾扎克的著作,走訪故居,做了數不清的石膏初稿,最後選擇了「披著睡袍仰頭思考」的形象,來表現巴爾扎克習慣夜間寫作的精神世界。
王魯湘:我們很多中國人甚至認為很可能羅丹這件作品,他的這樣一種簡約的,甚至是有點這個抽象的這種創作手法,是不是和我們中國水墨大寫意中間有一種聯繫,那麼羅丹有沒有受過東方藝術,特別是像中國藝術的影響?
卡特琳‧舍維約:羅丹是個充滿好奇心的人,他收藏了許多古文明的文物,共有6500件文物在我們的保管下,這是個很大的數量,在這些文物裡有一小組來自中國的文物,其中包括一個小型陶瓷雕塑,我們可以想像這個文物可能成為《巴爾扎克》雕塑的一個靈感來源之一,也有其他的靈感來源也影響了他,例如《高更》的雕塑,羅丹的思維裡沒有先入為主的想法,他到處尋找表現力,包括在一些跟他完全不同的在文化背景裡,他完全有可能從歐洲以外的文化背景中尋找靈感,這符合他的性格。

羅丹最為人所知的幾件著名作品在問世最初,都無一例外地遭到非議,完成後的《巴爾扎克》也是如此。有些人認為作品太粗陋草率,雕像如同一個裹著麻袋片的老漢。法國文學協會在輿論嘩然之下,拒絕接受這個紀念像。在受到大眾的嘲笑與謳諷的同時,羅丹發表公開信為自己辯護:「《巴爾札克》這個大膽進行探索的作品,是我一生的頂峰,是我以全部生命奮鬥的結果,是我美學原理的集中體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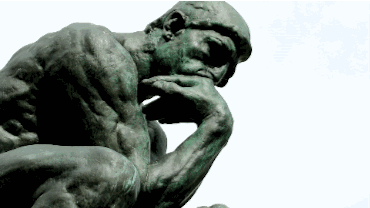
王魯湘:羅丹一定是個個性非常激烈的人。也就是說我們其實西方的雕塑從古希臘到羅馬開始,強調的是一種靜穆的美,一種古典的靜態的美。但是到了這個米開朗基羅開始,開始有一種動態的美,到了羅丹這裡,把這一種人體的動態的流動性的這樣一種美,其實提高到了一個很有力量的一種程度。那麼對羅丹這個人來說,他是不是更信奉power,信奉這種力量的表達。
卡特琳·舍維約:您說的對,米開朗基羅是他的一個榜樣,其實羅丹有兩個榜樣,一個是推動了他創作生涯的米開朗基羅,羅丹去了意大利,他發現了米開朗基羅,他非常推崇,米開朗基羅確實決定了羅丹後來大部分創作的方向,第二個榜樣是古希臘文明,他也同樣推崇,但他指的不是這些古文明的全部,而是特別指那些碎片型雕塑,這些考古發現的雕塑,是不完整的,羅丹感覺一個不完整的雕塑比一個完整的雕塑更有表現力,所以您說的對,是這種對錶現力量的不斷追求,在引導羅丹的創作。例如他當年習慣夜間舉著蠟燭帶領人們參觀他的工作室,用蠟燭照亮每一個大理石雕塑,以便突出每一處紋理,裂縫,由此展現雕塑作品最強的表現力和感染力,這種對最強表現力的追求,解釋了為什麼腳趾頭,臉部表情這些部位充滿緊繃感和扭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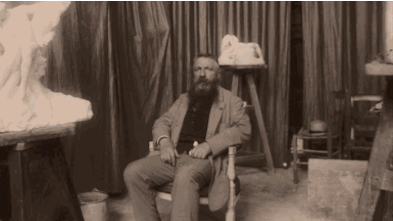
羅丹曾經這樣說過:「通常在自然中被稱為醜陋的事物,在藝術中卻能變成純粹的美。」後來這被稱為寫實主義美學,這一觀點對東西方近現代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在一百多年前,在羅丹身處的時代,他這樣的藝術追求,對於19世紀後半期歐洲中上層市民階級而言,太過超前。在那個時代,雕塑這種直觀的藝術形式裡,還不允許有「審醜」的事情發生。因此天才羅丹,在有生之年註定要活在毀譽參半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