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名臣名將系列之-「以一當十」的唐休璟
702年(武周長安二年),已連續激戰了30餘年的唐蕃兩國都有點打累,吐蕃使臣頻繁入長安請和。
武則天接待蕃使的過程中,發現這位蕃使屢次三番,將目光投向旁邊垂手而立的一位大臣。
便很奇怪的詢問何故,蕃使答道:「去年在洪源交戰時,這位將軍雄猛無比,殺了我們很多將士,因此想記住他的相貌。」
這位被吐蕃另眼相看的唐將,便是武則天時期出將入相的唐休璟,一位很多人都沒聽過名字的大唐名臣。
《舊唐書·唐休璟傳》:是後休璟入朝,吐蕃亦遣使來請和,因宴屢覘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眾,故欲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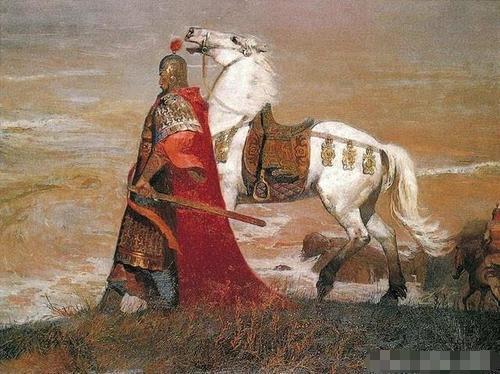
一、北抗突厥初出露機芒
唐休璟(627年-712年),名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今陝西興平)人,乃西涼國舅、北魏名臣唐和後商。
作為武則天時期的鎮邊名將,唐休璟曾任安西副都護、檢校庭州(新疆吉木薩爾)刺史、西州{ /b}(新疆吐魯番)都督,涼州(武威)都督、持節隴右諸軍州大使等職。
唐高宗永徽年間,唐休璟以明經科文職入仕,從吳王府的「典簽」,開啟了職業生涯。
但在典簽位置上,唐休璟沒顯示過人的才能,之後在綿州巴西尉、同州馮翊主簿任上,也是政績寥寥,乏善可陳。
679年(調露元年),沉寂多年的唐休璟得到了一個機會,這個展現價值的機會,也是個要人命的機會。
自貞觀四年(630年),唐軍一擊而亡東突厥後,差不多半個世紀的時期內,唐朝統治下的東突厥各部基本上穩定。
但由於,唐朝常年對外徵戰,不斷被抽調的突厥部落,不滿情緒漸漸累積,一些上層人物則滋生了復國的思想。
調露元年十月,單於大都護府下屬突厥酋長阿史那·德溫傅、阿史那·{b }奉職率所轄二部反唐,立阿史那·泥熟匐為可汗。
北部二十四州(羈縻州)的突厥酋長群起響應,反叛部落蜂集數十萬人,河東、河北諸道震動。
唐高宗遣宿將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兵討伐,但被阿史那·德溫傅擊敗,唐軍死傷萬餘,蕭嗣業戴罪流放桂州。
《新唐書‧蕭嗣業傳》: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
大敗唐軍後,突厥乘勝南下圍攻定州(河北定州)。
定州刺史李元軌(霍王,李淵第十四子)見突厥勢大,心知不可力敵,命人四門大開,偃旗息鼓,突厥疑有伏兵,反倒不敢深入。
《舊唐書李元軌傳》:「突厥來寇,元軌令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
就在這種危局之下,剛平定了西突厥可汗阿史那·都支的裴行儉再次出征。以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的職務,會同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合兵三十萬,轄制李思文和{ b}周道務帳下十八萬平叛。
唐軍旗幟綿延千里,《舊唐書》稱「唐世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營州(今遼寧朝陽)都督周道務,命已改任營州戶曹的唐休璟領兵迎戰,以呼應裴行儉的正面攻勢。
此時,深陷北方的營州已被突厥截斷道路,成了一支孤軍。
唐休璟的出戰,幾乎是個十死無生的計畫。
但在此危局面前,唐休璟迸發出前所未見的能力,率領孤軍在獨護山憑地形優勢,大破突厥,因功升任豐州(今內蒙古五原南)司馬。
《舊唐書·唐休璟傳》:「調露中,突厥背叛,誘奚、契丹侵掠州縣,後奚、羯胡又與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務遣休璟將兵,擊破之於獨護山,斬獲甚眾,超拜豐州司馬。
西元680年(唐高宗永隆元年)三月,裴行儉所部唐軍與突厥在黑山(今內蒙古包頭西北大青山)展開決戰。
突厥軍隊大潰,首領阿史那·奉職被俘,可汗阿史那·泥熟匐被部下殺死,獻首裴行儉帳前。
但此時,唐高宗李治認為突厥之指日可定,急令裴行儉班師回朝。
唐廷之所以急於召回北徵大軍,是因為吐蕃王朝已養虎為患。
就在此年,吐蕃在劍南方向攻陷了軍事重鎮茂州安戎城(四川茂汶西),嚴重威脅到了松州(松潘)、{ b}茂州(四川茂汶)、巂州(四川西昌)的安全。同時,在西域吐蕃再次佔據龜茲、疏勒等四鎮。
裴行儉班師後,突厥部落獲得了喘息之機,阿史那·伏念自立為可汗,同阿史那·德溫傅{/ b}合兵一處,繼續進犯唐境。
681年(開耀元年)正月,裴行儉再次以定襄道大總管的身份領兵平叛。
這次,他沒有強攻而是用反間計,誘使阿史那·伏念與阿史那·德溫傅互相猜忌。
新任突厥可汗阿史那·伏念心中恐懼,在得到裴行儉「歸降不殺」的承諾後,綁了阿史那·德溫傅到營前請罪,突厥就此悉數平定。
但可惜,高宗李治違背了裴行儉的承諾,阿史那·伏念、阿史那·德溫傅均被處死。
裴行儉聞後嘆息道:「西晉的王渾,嫉妒王濬平定吳國的功勞,古今皆以為恥。只怕殺掉降將以後,就再無願降之人了!
《舊唐書‧裴行儉傳》: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為程務挺、張虔勗肋逐,又磧北迴紇逼之,計窮而降。行儉之功不錄。封聞喜縣公。行儉曰:「渾曰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

果不出裴行儉所料,次年「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那·元珍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入寇並州及單於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茂。
弘道元年(683)「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乙亥,復寇媯州(河北省涿鹿縣西南)。三月,阿史那·骨篤祿、阿史那·元珍圍單於都護府,執司馬張行師殺之。
「五月,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河北蔚縣),殺刺史李思儉,豐州(內蒙古五原縣南)都督崔智辯將兵速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為虜所擒。
突厥圍攻豐州,斬殺崔智辯,領唐廷震動,多數唐臣都主張放棄豐州,將百姓南遷至靈州(寧夏靈武)、夏州(陝西靖邊)一帶。
恰在豐州司馬任上的唐休璟,上表力陳不可:「豐州自秦漢便是國家重鎮,土地肥沃,適合農牧生產。
隋末大亂,將百姓遷至寧慶二州,致使胡寇深入,以靈夏二州為邊境。貞觀末年,朝廷移民充實豐州,西北方才得以安寧。
今若廢豐州,黃河將再為胡寇所有,靈夏等州亦不能安居,斷非國家之利。 ”
《舊唐書·唐休璟傳》: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歿。朝議欲罷豐州,徙百姓於靈、夏。
休璟以為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遏賊,實為襟帶,自秦、漢已來,列為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為邊界。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
唐休璟的上書否定許多唐臣苟安的思想,沒有積極進取的邊疆政策,一味綏靖苟安,只會導致邊境軍事壓力越來越大。
還好,唐庭採納了唐休璟的建議,面對突厥的壓力,針鋒相對的加大了唐軍反擊的力度,將豐州這個黃河北岸的戰略支撐點牢牢守住。
唐休璟長於局勢判斷,又積極進取的鎮邊思路,讓其從眾多邊將中脫穎而出。
不久,唐朝中央政治版圖的變化,將他帶到了一個更兇險的戰場-直面吐蕃。

二、直面吐蕃以一當十
永淳二年(683年)高宗去世,武則天實際執政。調露元年(679年)起任安西都護的王方翼、庭州刺史的杜懷寶等人,雖戰功卓著,但由於王方翼與王皇后是近親,又牽連於裴炎、程務挺一案,很快被召回朝廷解除實權。
武則天執政後透過更換邊將,啟用大批中低階將領,一方面是剪除舊勢力,同時也希望對外能重新開拓新的格局。
唐休璟正是在這種政治格局下,以長期鎮守邊疆的經歷,又無家族勢力干擾,被武則天提拔為安西副都護檢校庭州刺史{/b }。
此時,吐番國內自芒松芒贊逝世後,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內亂,對外擴張的步伐明顯放緩。
但在初步穩定局面後,論欽陵重拾以戰養戰的策略,不斷在西域發動攻擊。
689年(永昌元年),武則天命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徵討吐蕃。
但吐蕃統帥論欽陵早有防備,在沿途堅壁清野,導致勞師遠徵唐軍糧草不續。
七月,韋待價在寅識迦河(今新疆伊寧西南)與吐蕃激戰期間,恰逢大雪,副將閻溫古逗留不進,致使唐軍慘敗。
論欽陵順勢攻克焉耆(新疆焉耆)等地,韋待價無奈,只好率軍退回西州(新疆吐魯番高昌故城)屯駐,
武則天處斬閻溫古,流放韋待價後,急劇惡化的西域殘局只能由唐休璟來收拾。
他一方面「收其餘眾」穩定人心,另一方面從庭州(新疆吉木薩爾)趕赴西州,抵抗吐蕃一輪又一輪的狂攻。
憑藉著出色的善後工作,武則天親點他升任西州都督,進一步得到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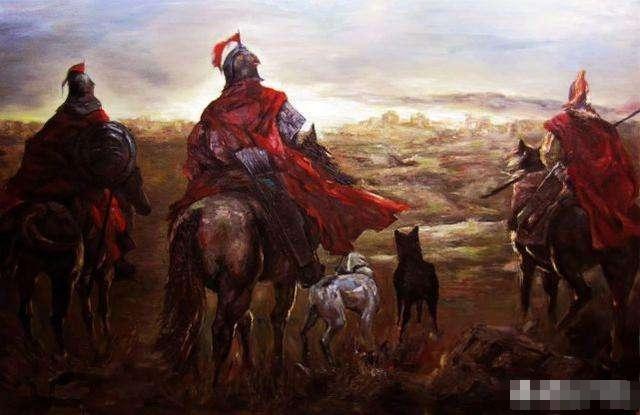
692年(長壽元年)前後,西域情勢再次改變。
隨著,吐蕃國內君權與相權間的摩擦愈演愈烈,西域各部落紛紛倒向唐朝。
敏銳察覺到局勢變化的唐休璟,上書武則天請求派兵再次收復安西四鎮。
王孝傑與阿史那·忠節在周邊部落軍隊的配合下,大敗吐蕃軍隊,一舉收復了安西四鎮,於龜茲{/ b}置安西都護府,以3萬唐軍鎮守。
徹底改變了22年間,安西四鎮六度易手的局面。
戰後論功行賞,朝野皆以為「(王孝傑)破吐蕃,拔四鎮,實賴休璟之謀」,故在西州為其刻石建碑,並召其入朝主政靈州(甘肅靈武)。
700年(久視元年),已升任持節隴右諸軍州大使,兼涼州(甘肅武威)都督的唐休璟,再次直面吐蕃的進攻。
當時,把持吐蕃朝政50年的噶爾家族已經覆滅,吐蕃軍神論欽陵自殺,其弟贊婆,子論弓仁{/ b}降唐。
這次率軍進犯的是吐蕃大將麴莽布支,蕃軍兵至洪源谷,打算圍攻昌松縣(甘肅武威東南)。
唐休璟率軍迎擊,他見吐蕃軍衣甲鮮盛,對部將道:「麴莽布支麾下皆貴族子弟,雖然軍容強盛,乃不通軍事之輩,且看我如何破敵。
言畢,唐休璟披甲先登,直取中樞,六戰六克,大敗吐蕃,斬其副將二人,獲首二千五百級,並積屍做京觀。
《舊唐書·唐休璟傳》:久視元年秋,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
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婆降,麴莽布支新知賊兵,欲曜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
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克,大破之,斬其副將二人,獲首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
這就是前文蕃使入朝後,不斷以目窺視唐休璟,並言「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眾,故欲識之。
可見,在吐蕃君臣心中,唐休璟已成一員值得敬畏的唐將。
很多時候,敵人的敬重才是最好評價。 武則天心花怒放之餘,對唐休璟愈發看中。

703年(長安三年)突騎施首領烏質勒與西突厥失和,西域各部落間刀兵四起,致使安西四鎮和關中的聯繫斷絕。
武則天令唐休璟與宰相商討如何應對,只片刻間,唐休璟就拿出了方案。
十多天后,安西諸州報告朝廷,前方的情況與唐休璟的描述完全一樣。武則天不由得感慨道:「恨用卿晚」。
隨後,她又對其他大臣說:「休璟諦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舊唐書·唐休璟傳》: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公頃間草奏,便遣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台三品。又謂魏元忠及楊再思、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諦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唐休璟之所以能料敵千里之外,皆賴其長期鎮邊期間,曾仔細研究過各部落間的關係的周邊地形地貌,甚至連一山一壑、一關一卡都不放過。
正如《舊唐書·唐休璟傳》所言:「休璟尤諳練邊事,自碣石西逾四鎮,綿亙萬裡,山川要害,皆能記之」。
萬裡邊關皆在胸中,才讓他做到了,「共服戎虜,不憂邊陲,以一當十」。
參考書目:
《資治通鑑‧唐紀》;
《兩唐書·唐休璟傳》;
《兩唐書·唐休璟傳補闕》_薛宗正;
《唐休璟與武週年間的西北邊防》_張重洲
本文為網易新聞·網易號家鄉特色簽約內容
詳解歷史細節,釐清來龍去脈,視角不同的中國歷史!
歡迎關注“白色發布衣的藏地讀行!”

